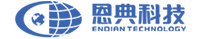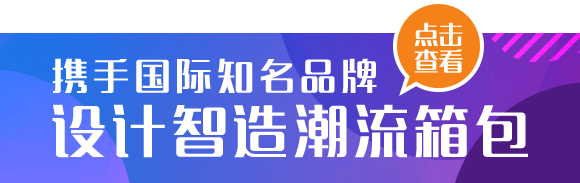03年南下的大巴上,我帮了对高烧的母子,她下车时塞给我一张手刺:小伙子,年后别打工了,来深圳找我,你必定会有好报的
创造声明:本文为虚拟故事。文中角色行为、职场情节等均为情节需求,不代表作者观念,亦非实在的日子辅导。请读者理性看待。
在2003年那趟拥堵炽热的南下大巴上,我把最终的退烧药和仅有的瓶装水,递给了那个抱着高烧孩子的生疏大姐。
她感谢得热泪盈眶,临走时,奥秘地塞给我一张手刺,在我耳边留下一句滚烫的承诺:“小伙子,年后别打工了,来深圳找我,你必定会有好报的!”
一年后,当我被工厂的流水线磨掉一切棱角时,这句话成了我对立失望的仅有稻草。
可深圳那么大,人海茫茫,一个素昧平生的承诺,究竟是改变命运的船票,仍是一个永久无法实现的空想?

车厢里塞满了人,空气中混合着汗液发酵的酸味、廉价卷烟的呛味,还有隔夜泡面那股挥之不去的油腻气味。
窗外的景象单调地向后奔驰,无尽的郊野和偶然闪过的村庄,都和他死后那个生养他二十年的家园没什么两样。
他本年二十一岁,揣着爹妈东拼西凑来的六百块钱,还有几件换洗的衣裳,一头扎进了这南下的激流里。
在老家,他跟着三叔在建筑队上干活,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散架,也挣不了几个钱。
同村的二狗上一年去了深圳,春节回来时穿戴簇新的夹克衫,手腕上戴着一块亮晶晶的电子表,说起外面的国际,眼睛里满是光。
他不清楚深圳是啥姿态,也不理解自己能做什么,只理解不能再像曾经那样活。
李文浩抬起头,看见一个穿戴朴素蓝布褂子的大姐,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。
那孩子满脸通红,嘴唇干裂,脑袋无力地耷拉在大姐的膀子上,整个人像一棵被烈日晒蔫了的小草。
“宝儿,再忍忍,喝点水……”她拧开一个旧水壶,递到孩子嘴边,可孩子仅仅难过地哼唧着,把头埋得更深了。
周围几双耳朵马上竖了起来,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那对母子,目光里不再是漠然置之,而是添了几分警觉和嫌恶。
2003年,那场席卷全国的“非典”风云尽管已逝去,但留在人们心里的暗影还未散尽。
“离远点,别再感染了!”斜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嘟囔了一句,还夸大地用手捂住了口鼻。
司机关掉响彻云霄的音乐,透过后视镜不耐烦地吼了一句:“咋回事啊?看好自己的孩子,别在车上捣乱!”
大姐的脸瞬间涨得通红,抱着孩子的手臂又收紧了几分,像是想把孩子藏起来,不让那些刺人的目光损伤到他。
他没理睬周围的闲言碎语,从自己的帆布包里翻出了一个还没开封的塑料袋,里边装着他娘给他预备的、簇新的白毛巾。
他又拿出自己省着喝的一瓶矿泉水,这水在车站卖两块五,他疼爱了良久才买下。
他拧开瓶盖,把清亮的水倒在毛巾上,浸湿了一大半,然后挤上前去,递给那位大姐。
“大姐,别急。用这个湿毛巾给孩子擦擦脑门、脖子和胳膊窝,能降降温。”他的声响不大,但很沉稳。
冰凉的毛巾敷在滚烫的皮肤上,孩子舒畅地哼了一声,紧绷的小脸好像舒缓了一些。
李文浩又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用纸包着的小药包,打开来,是几片白色的药片。
“这是退烧的。我本来是怕自己不服水土预备的。你掰半片,想办法让他喝下去。”
“没事,救急要紧。”李文浩把药塞到她手里,又帮她把孩子扶正,好让她喂药。
在他的协助下,那大姐又是喂药又是物理降温,折腾了半个多小时,孩子的体温总算降下来一些,呼吸也逐渐平稳,在大姐的怀里沉沉睡去。
临下车前,她从随身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里,翻找了半响,摸出一张簇新的手刺,箭步走到李文浩身边,一把塞进他手里。
她凑到他耳边,压低了声响,口气却无比慎重:“小伙子,大恩不言谢。你是个好人,将来在工厂里静心干活太屈才了。过了年,你别急着找活儿干,拿着这个,来深圳这个地址找我。你必定会有好报的。”
李文浩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手刺上的字,大姐现已抱着孩子挤下了车,敏捷汇入了站台喧闹的人流中,转瞬就不见了踪迹。
他垂头摊开手掌,一张规划简略的白色卡片静静地躺在手心,上面印着几行字:深圳市华美交易有限公司,司理,陈静。
他无法确认这句“必定会有好报”是真是假,但这句温暖的话,却像一束光,照进了他苍茫的旅途。
深圳,这座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,给李文浩的第一个见面礼,是兜头一盆冷水。
二狗嘴里的“轻松活”,是每天站在轰鸣的流水线旁,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上万次——将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零件,精准地电路板的卡槽里。
晚上睡觉,此伏彼起的鼾声和呓语,让他这个在乡村听惯了蛙鸣长大的孩子,夜夜难以入睡。
说好的一千二底薪,扣掉住宿费、水电费,再碰上几回平白无故的罚款,到手往往缺乏八百。
二狗早就没了春节回家时的神情,他拍着李文浩的膀子,苦笑着说:“兄弟,这便是深圳。忍着吧,咱们都这么过来的。”
为了省钱,他一天三顿都在食堂吃最廉价的白菜和冬瓜,连买一瓶汽水都觉得是奢华。
那张归于“陈静”的手刺,被他用塑料纸小心肠包好,夹在了一本翻烂了的《读者》杂志里。
这本杂志是他仅有的精神食粮,而这张手刺,则是他对立实际疲乏的最终一点念想。
无数个加班到深夜的晚上,宿舍里的人都睡熟了,他会借着窗外朦胧的路灯火,悄然拿出那张手刺,指尖在“陈静”两个字上重复摩挲。

他甚至有一次鼓起勇气,跑到厂区门口的公用电话亭,对着手刺上的号码,按下了几个数字,但手指在最终一个键上悬了半响,终究是寂然地挂上了听筒。
他怕,怕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句“你打错了”,或许更糟的,“你是谁啊,我不认识你”。
李文浩也盼着,他算着自己这一年攒下的钱,够给爹妈买件新衣裳,再给弟弟买个他想念了好久的文具盒。
可就在发薪日的前一天,车间主管忽然宣告,由于公司困难,这个月的薪酬和年终奖都要推迟到年后发放。
有人在默默地抽烟,有人在低声诅咒,还有人渐渐的开端拾掇行李,预备第二天拿不到钱就走人。
李文浩的老乡二狗,那个最初把他带到深圳的人,红着眼睛对他说:“文浩,哥对不住你。这鬼地方,无法待了。我明日就回老家,再也不出来了。”
他从自己仅剩的日子费里,拿出一部分,去镇上的小摊,买了一件最廉价但看起来还算整齐的白衬衫和一条深色裤子。
他对着宿舍那面含糊的破镜子,一遍遍地收拾自己的衣领,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李文浩坐着波动的中巴车,花了快两个小时,才依照手刺上的地址,找到了那栋名为“国贸大厦”的写字楼。
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穿戴笔挺西装、踩着高跟鞋的男男女女们步履仓促地进出,空气中都似乎弥漫着一股与工厂区天壤之别的、精明而高效的滋味。
他站在大厦门口,看着自己脚上那双沾了少许泥点的旧皮鞋,又看了看自己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,一股自卑感情不自禁。
他攥了攥拳头,挺直了腰板,学着那些城里人的姿态,跨步走进了富丽堂皇的大堂。
大堂里铺着能照出人影来的大理石地板,中央空调吹出的凉气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“先生,请问你找谁?”保安的口气还算谦让,但那份职业性的警觉却清楚明了。
“我……我找华美交易有限公司。”李文浩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有些褶皱的手刺,递了曩昔。
她接过李文浩的手刺,抬起眼皮打量了他一下,那目光让李文浩觉得脸上辣的。
“你找陈静司理?有预定吗?”前台小姐的声响洪亮,却带着一丝不易发觉的疏离。
“没……没有预定。”李文浩严重地搓着手,“是她让我来的。咱们在车上见过。”
她拿起电话,拨了一个内线号码,对着话筒低声说了几句,期间还昂首看了李文浩两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