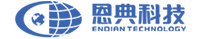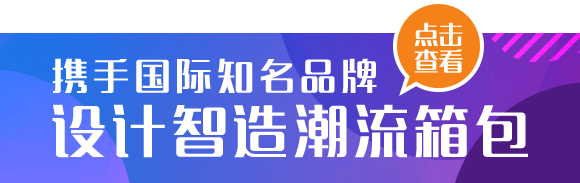黑压压的人群骚动起来,只见大秦太后赵姬,披头散发,竟真的如一头疯狂的母兽,撞开了千名禁军用长戈组成的铁壁。她跪倒在泥地里,朝着高台上那个自己亲生的、却冷酷如冰的儿子,用尽最后的尊严哀求:
高台上的嬴政面沉如水,看着母亲为了那个男的丑态百出,嘴角甚至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。这正是他想要的羞辱,是他亲手导演的戏剧。
然而,就在此刻,那个即将被车裂的男人,那个一直沉默的嫪毐,突然用尽全身力气,从怀中亮出了一件东西。
年轻的秦王龙体巨震,脸上所有伪装的冷静瞬间崩塌,他指着台上的嫪毐,发出了受伤野兽般的咆哮:

只有风在巷子里打转,卷起地上的烂菜叶和灰尘,呜呜地响,像是谁家死了人,在办丧事。
章台宫里,比外面还要安静。熏香早就停了,空气里只有铜器和木头发出的陈旧味道。嬴政坐在案前,面前摊着一卷竹简。
他看着嬴政的手,那只手骨节分明,年轻,但握笔的姿势却像个老人一样,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。
李斯的身子又低了些,说:“太后……自从知道那两个……孩子被处置了以后,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寝宫里。不吃不喝,只是哭。有时候也砸东西。”
“哭?”嬴政的嘴角似乎动了一下,像是在笑,又不像,“她还有眼泪可以流。那就让她哭。传我的命令,把她挪到甘泉宫去,没有我的准许,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让她对着空荡荡的宫殿,好好哭个够。”
他的声音很平,平得像一潭死水,听不出一点波澜。仿佛在说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女人的事。
嬴政画完了最后一个叉,把笔放下。他站起身,走到窗边,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。咸阳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囚笼,而他就是那个唯一的掌管钥匙的人。
“时辰快到了。”嬴政说,声音不大,却传遍了空旷的大殿,“让监斩官准备。我要亲自去高台上看着。我要让咸阳所有人都看着,让六国所有的探子都看着。背叛寡人,背叛大秦,是什么下场。”
他要让她亲眼看着,看着她不顾一切去爱的男人,是如何像一滩烂肉一样,在自己眼前被撕碎。他要用最残忍的方式,斩断她所有的念想,也斩断自己心里最后一点可笑的、残存的温情。
高高的木台上,竖着几根粗大的柱子,上面拴着冰冷的铁链。台下,黑压压的都是人头。百姓们远远地站着,伸长了脖子,脸上是既害怕又兴奋的表情。他们想看,想看那个传说中睡了太后、还想当秦王爹的男人,到底长什么样,又是怎么个死法。

赵姬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母狼。她曾经引以为傲的满头乌发,现在乱得像一蓬枯草,随意地披在肩上。华美的宫服被她自己撕得破破烂烂,露出里面苍白的皮肤。她的指甲因为抓挠墙壁和柱子,已经断裂,渗出血丝。
地上全是碎裂的瓷器和玉器,那些曾经让她赏心悦目的东西,现在都成了她发泄痛苦的工具。两个孩子……她和他的两个孩子……她一闭上眼,就能看到他们小小的身体,被嬴政的武士装在麻袋里,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。那一声沉闷的响动,像是直接砸在她的心脏上。
她不恨那些武士,他们只是奉命行事。她恨嬴政。她那个冷得像冰块一样的儿子。
他的心是石头做的吗?那是他的亲弟弟啊!虽然是不该出生的弟弟,但那也是血脉相连的弟弟啊!
“政儿……政儿……”她喃喃自语,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在摩擦,“你怎么能这么狠心……”
可恨意过后,是更深的恐惧和思念。她想到了嫪毐。那个让她重新活过来的男人。
在没有他的日子里,这座华丽的宫殿就是一座坟墓。她只是一个挂着太后名号的活死人。
是他,用他那带着市井气息的、滚烫的身体和同样滚烫的心,让她感觉自己还是个女人,一个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女人。
他说:“姬,等我们的儿子长大了,就让他当王。我们去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国。”
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,就像野草一样疯狂地生长。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咸阳的刑场上。她要救他。哪怕救不了,她也要去见他最后一面。她要告诉他,她不后悔。
她拉开一个个抽屉,把里面所有值钱的首饰、珠钗、玉佩全都扫进一个布包里。这么多东西,是秦王赏的,是先王赏的,是吕不韦送的。它们代表着她作为政治工具的一生。
她叫来一个贴身的老宦官。这个宦官是她从赵国带过来的,是唯一还能信得过的人。
“拿着这些,”她把沉甸甸的布包塞到他怀里,“去收买宫门的卫兵。不管花多少钱,告诉他们,我只要出宫一个时辰。就一个时辰。”
老宦官吓得跪在地上,浑身发抖:“太后,使不得啊!大王下了死命令,您……”
“让你去就去!”赵姬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火焰,那是一种混合了疯狂和决绝的光,“我不是在跟你商量!要么你帮我,要么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这里!”

嬴政执黑子,李斯执白子。李斯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,他每下一步,都要思考很久。而嬴政却显得很随意,他捻起一颗黑子,几乎不假思索地落下,清脆的“啪”一声,就截断了白子的一大片生路。
“不是棋艺精湛,是你不敢赢。”嬴政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很平静,却让李斯感觉像是被一把刀子刮过皮肤。“你在担心太后。你觉得寡人做得太绝了。”
李斯连忙跪下:“臣不敢!太后与嫪毐叛乱,罪证确凿,危及社稷。大王拨乱反正,乃是天经地义,臣只有拥护之心,绝无半分异议。”
嬴政没让他起来。他伸出手,将棋盘上的棋子一颗一颗地捡回到棋盒里。黑色的,白色的,混在一起,再也分不清彼此。
“寡人知道,很多人都在背后说寡人冷血,不孝。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囚禁起来,连那两个孽种……都毫不留情。”他的声音依然平稳,“他们不懂。寡人若不这么做,天下人会怎么看我?怎么看我大秦王室?他们会说,秦王嬴政是个连家事都管不好的懦夫,他的母亲可以随意与人私通,生下的野种还可以觊觎王位。如此,寡人还如何号令天下,如何让六国畏惧?”
“所以,今天这一场,必须要做得漂漂亮亮。不仅要杀嫪毐,还要诛心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,这片土地上,只有一种意志,那就是寡人的意志。任何情感,任何亲情,在王权面前,都一文不值。”
他终于看向李斯,眼神里带着一丝洞悉一切的冷酷:“你以为,寡人派去甘泉宫的千名铁鹰锐士,只是为了看守她吗?”
李斯猛地一抬头,眼中充满了震惊。铁鹰锐士,那是大秦最精锐的部队,是嬴政的嫡系心腹,每一个都以一当十。用这样的力量去看守一个手无寸铁的太后,简直是……
“你错了。”嬴政将那颗黑子丢回棋盒,发出“嗒”的一声轻响。“他们不是去看守她,也不是去阻拦她。他们是……去迎接她的。”
“寡人知道她会来。她一定会来。”嬴政站起身,走到地图前,那是一幅巨大的秦国地图,上面还标注着东方六国的疆域。“她会像个疯子一样冲向刑场,为她的男人求情。而寡人,就要让咸阳的百姓,让六国的探子,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幕。看到大秦的太后,是如何为了一个卑贱的弄臣,而丑态百出。”
“寡人要让她自己把最后一丝尊严都撕碎。要让她在万民的注视下,看着她的男人被一寸寸地撕裂。我要让她明白,她的爱,她的恨,她的眼泪,在寡人这里,什么都不是。寡人要让她,彻底心死。”
李斯伏在地上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终于明白了。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行刑。
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、针对太后赵姬的公开处刑,也是一场嬴政对自己的过去的彻底埋葬。
他不是在杀一个嫪毐,他是在用嫪毐的血,来祭奠那个曾经还对母爱抱有幻想的、名叫“政儿”的少年。
嬴政不再说话,宫殿里又恢复了死寂。只有窗外的风声,越来越凄厉。一张无形的大网,已经在咸阳城上空张开,而网的中心,就是渭水桥边的刑场。

空气中混合着霉菌、腐烂的稻草、血和屎尿的味道,熏得人想吐。老鼠在墙角肆无忌惮地跑来跑去,发出“吱吱”的叫声,像是在嘲笑这里关着的将死之人。
嫪毐被锁在一个最深处的牢房里。他的四肢都被粗大的铁链锁着,琵琶骨也被穿透了,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。他身上基本上没有一块好皮,布满了鞭痕和烙印,有些地方的伤口慢慢的开始腐烂,发出恶臭。
这几天,他经历了所有他能想象到的酷刑。廷尉府的那些人想从他嘴里撬出更多关于吕不韦的事情,但他什么都没说。不是他有多忠诚,而是他知道,说了也是死,不说也是死。既然都是死,何必再说那些废话。
他的身体被折磨得不成样子,但他的脑子却异常清醒。他会想起很多事。想起自己还在街头当混混的时候,每天想的只是怎么填饱肚子。想起被吕不韦的人找到,让他假扮宦官进宫。想起第一次见到赵姬,那个高高在上、眼神却像一潭死水的女人。
他记得她是怎么一步步依赖上自己的。起初,她只是需要一个能让她忘记寂寞的工具。但渐渐地,她的眼神变了。那潭死水活了过来,开始有了波澜,有了温度。她会对着他笑,会给他讲她小时候在赵国的故事,会像个小女孩一样,枕着他的胳膊,说些不切实际的梦话。
他也陷进去了。他享受着太后的宠爱,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迷醉。他甚至开始觉得,自己是真心爱上了这一个女人。他们的两个孩子出生后,他的野心和父爱交织在一起,膨胀到了极点。他真的以为,自己能成为这一个国家的新主人。
牢门上的小窗被打开了,一张脸凑了过来。是那个前两天被他用藏在鞋底的最后一颗珍珠买通的狱卒。
狱卒警惕地朝外面看了看,然后飞快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破布包着的小东西,从窗口塞了进来。
“就这一次,以后别再找我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”狱卒说完,立刻关上了小窗,脚步声匆匆远去。
嫪毐用尽全身力气,挪动着身体,将那个小布包捡了起来。他没有打开看,只是用被血污和泥垢覆盖的手,紧紧地攥着它。布包很小,隔着布料,可以感觉到里面东西的轮廓,硬硬的,有棱有角。
他把它小心地塞进了自己破烂囚衣最里面的夹层,紧紧地贴着胸口的皮肤。那里是唯一还算干净的地方。
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。车裂之刑,他听说过,那是把人活活撕成碎块。他不怕死,但他不甘心就这么窝囊地死去。他要在这场必输的棋局里,落下最后一颗棋子。这颗棋子杀不了对方的王,但足以在棋盘上,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裂痕。
他要让那个高高在上的秦王嬴政,在他死后,每一次呼吸,都能感觉到这道裂痕带来的疼痛。
他闭上眼睛,黑暗中,仿佛又看到了赵姬的脸。她的笑,她的泪,她在他耳边说的情话。他低声笑了笑,牵动了嘴角的伤口,一阵钻心的疼。
姬,对不住了。我要用你给我的这件东西,去刺你儿子最深的一刀。这也是我……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
嫪毐睁开眼,眼神里没有了恐惧,只剩下一种近乎疯狂的平静。他知道,最后的时刻,到了。

行刑的高台就搭在桥中央,像是给这座古老的桥梁戴上了一顶血腥的王冠。台下,黑压压的人群像退潮后沙滩上的海藻,密密麻麻,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。人们的脸上混合着各种表情,有麻木,有好奇,有恐惧,还有一丝隐藏不住的兴奋。他们像是在等待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,而不是一场残酷的屠杀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桥的一头。一队身穿黑色铠甲的士兵,手持长戈,押着一辆囚车,缓缓驶来。囚车是木头做的,很简陋,上面站着一个披头散发、浑身血污的人。那就是嫪毐。
他身上的囚衣已经变成了暗红色,被血和泥粘在身上。他被铁链锁在囚车的柱子上,每走一步,铁链就发出“哗啦”的声响,像是在为他奏响送葬的哀乐。他低着头,看不清表情,但那具虽然残破却依然站得笔直的身体,透着一股不肯屈服的劲儿。
囚车在台下停住。两名刽子手跳下高台,他们长得人高马大,赤裸着上身,古铜色的皮肤在阴沉的天光下泛着油光。他们粗暴地打开囚笼,把嫪毐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出来,然后架上高台。
另一队人马从桥的另一头出现了。为首的,是一面巨大的黑色龙旗,在风中猎猎作响。旗帜下,是一队队身披重甲的禁军,他们步伐整齐,杀气腾腾,像一道移动的钢铁城墙。在他们的簇拥下,一个身穿黑底金纹龙袍的年轻人,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,缓缓而来。
他今天没有坐王辇,而是选择了骑马。他年轻的脸庞在灰色的天光下显得异常白皙,表情冷峻得像一块万年不化的寒冰。他没有看台下的任何人,径直骑到高台正对面的一个监斩席上。那是一个比刑台稍矮一些的台子,铺着华丽的毯子。他下了马,一言不发地坐下,目光像两把利剑,直直地射向台上的嫪毐。
监斩官走上高台,展开一卷竹简,用尽全身力气,一字一句地宣读着嫪毐的罪状。
“伪宦嫪毐,秽乱宫闱,与太后私通,诞下孽子……”声音通过某种简陋的扩音装置,传遍了整个渭水桥。人群中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和议论。虽然早有耳闻,但当这些罪状被官方如此直白地宣读出来时,带来的冲击力还是巨大的。
“……结党营私,窃用国玺,意图谋反,罪不容诛!”监斩官读完最后一句,将竹简狠狠摔在地上。“奉大王令,处以车裂之刑,以儆效尤!”
嫪毐被刽子手们绑在了五根柱子上,四肢和头颅各拴一根粗绳,绳子的另一头,连着五匹高大的骏马。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,只是抬起头,环顾四周。他的目光越过黑压压的人群,越过那些冷冰冰的士兵,像是在寻找什么。
监斩官看了看天色,又看了一眼监斩席上的嬴政。嬴政面无表情,只是微微抬了一下手。

就在监斩官手中的令箭即将脱手的那一刹那,人群的尽头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、不似人声的哭喊。
这声音凄厉得像一只受伤的杜鹃在泣血,穿透了数千人的喧嚣和风声,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
人群像被投入石子的水面,瞬间骚动起来。人们纷纷回头,只见一个女人,披头散发,衣衫凌乱,正疯了一样地从远处冲过来。她身后跟着几个同样衣着狼狈的宫人,但很快就被后面追上来的卫兵按倒在地。只有那个女人,像一支出弦的利箭,凭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,竟然真的冲破了外围的防线。
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更大的哗然。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身的眼睛。那个传说中尊贵无比的秦国太后,竟然会以这样一种狼狈不堪的姿态,出现在这种场合。
嬴政早就料到她会来,但他没想到她会来得这么快,这么不顾一切。他布置在咸阳各处的关卡,那些他以为能稍微阻碍她一下的卫兵,在她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。
上千名守在刑场核心区域的铁鹰锐士立刻行动起来,他们没拔刀,而是迅速组成一道人墙,手中的长戈交叉,形成一片密不透风的钢铁丛林,将那个疯狂的女人死死地挡在了刑台十丈之外。
她撞在冰冷的长戈组成的墙上,被反弹回来,摔倒在地。但她立刻又爬起来,用手去推那些长戈,哭喊着,哀求着。
她看到了高台监斩席上的嬴政,那个她身上掉下来的肉,她唯一的儿子。她用尽全身的力气,朝他跪了下来,在冰冷的石板上磕头,一下,又一下,很快额头就渗出了血。
“政儿!母后求你了!放过他吧!一切都是我的错,跟他没关系!你要杀就杀我!他是无辜的!”
她的哭喊声回荡在渭水桥上,带着无尽的绝望和哀求。人群死一般地寂静,所有人都被这超出他们想象的一幕惊呆了。儿子要杀母亲的情人,而母亲跪在地上为情人求情。这比任何戏文里的故事都更加荒唐,更加震撼。
高台上的嬴政,身体坐得笔直,像一尊雕像。他的手紧紧地握着座椅的扶手,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他看着那个在地上磕头、哭得涕泪横流的女人,那个曾经抱着他、唱着歌谣哄他睡觉的母亲,如今为了另一个男人,在他面前,在万民面前,抛弃了所有尊严。
他心中最后一点名为“亲情”的东西,正在一寸寸地碎裂,变成冰冷的粉末。他的眼神越来越冷,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。他没有说话,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。
禁军们会意,他们没伤害赵姬,只是用戈柄将她牢牢地拦住,让她无法再前进一步。
赵姬看着那些冷漠的脸,看着高台上纹丝不动的儿子,她终于明白了。她的一切哀求都是徒劳的。她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,瘫倒在地。

就在这时,一直沉默不语、像个死人一样的嫪毐,突然动了。他猛地抬起头,用尽全身的力气,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。这声嘶吼充满了不甘和疯狂,瞬间压过了赵姬的哭声,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
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,他挣扎着从破烂的囚衣内襟里,掏出了一个东西,高高举起...
它不是金银珠宝,在阴沉的天光下没有反射出任何光芒。它也不是什么兵符或者信物,上面没有复杂的纹路。
因为常年被人摩挲把玩,它的表面已经变得异常光滑油亮,棱角都被磨圆了,透着一股时间的温度。
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们想不通,这个即将被五马分尸的死囚,为何会在临死前,亮出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。
跪在地上的赵姬,在看到那只木老虎的瞬间,哭声就像被一把无形的剪刀剪断了,戛然而止。
她的瞳孔在刹那间放大到极限,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,变得像纸一样惨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