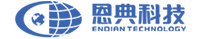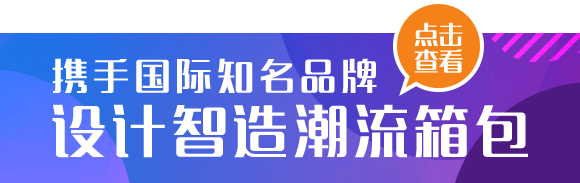王成功那句“饿不死”,像一根细微的冰针,精准地扎进了我心里最不设防的当地。
那十万块钱,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笔巨款,但对我爸,那是当年预备给我爷爷治病的救命钱。
似乎我从一个或许带来必定的优点的“陈总”,瞬间变回了那个光着在村里跑的“二娃子”。
脱离伯父家,走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上,晚风吹在脸上,带着山里特有的草木幽香。
我拿出从城里带回来的专业测绘东西,卷尺、标杆、水平仪,一整天都泡在那片山上。
我认为,这样的日子会继续好久,直到我把农庄建起来,用现实堵住所有人的嘴。
他满头大汗,目光躲闪,不敢看我,手里还紧紧抱着一个用旧布包裹得结结实实的东西。
没等我反响过来,他现已拉开门,一溜烟地跑了出去,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。
今日,这个赖了五年账,我爸提一次他就哭穷一次的老赖,居然连夜把钱还了回来?

我坐在床边,看着这堆钱,大脑一片紊乱,完全没有办法将它们和王成功联络在一起。
他素日里游手好闲,靠着在镇上打零工和四处借钱过日子,是村里有名的“困难户”。
三姨、四叔、堂哥……一张张了解的面孔,全都挤在门口,窃窃私语,神色着急。
我完全傻眼了,感觉自己像个忽然中了大奖的幸运儿,但又觉得这奖品棘手得很。
亲属们众说纷纭,每个人都想从我嘴里套出点什么,目光里闪烁着贪婪和巴望的光辉。
我总算理解,王成功昨夜的失常,和今日这怪异的“还钱潮”,背面必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工作发生了。
打发走这群热心的“财神爷”,我关上院门,看着屋里桌子上堆成小山的一堆现金。
我把钱锁进一个旧铁皮箱里,藏在床下,然后锁好门,朝着村东头的赵永强家走去。
他靠着这几年乡间盖房热,在村里开了个建材店,赚了不少钱,是村里的“能人”。
“永强,你这音讯靠谱吗?别是瞎说的吧?”一个乡民叼着烟,将信将疑地问道。

“陈立文,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!要不是我嘴快,你该不会是就想一个人把这天大的优点给独吞了?”
“我便是想回来建个农庄,自己种种田,养养鱼。你们说的什么几十亿出资,我底子就不知道!”
所有人都确定我掌握着一个惊天的隐秘,我的任何解说,在他们看来,都成了相得益彰的粉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