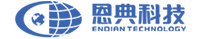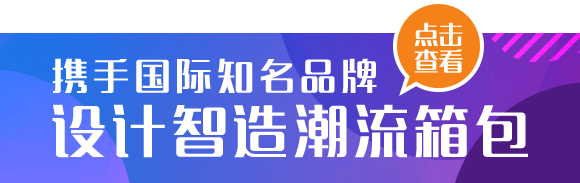二十年了,他们的对话总是这样。像两根被水泡得发白、再也拧不到一块儿的烂木头。
直到她快要咽气的时分,他才发现,母亲不是被时刻泡烂的,她是自己沉到了水底,水底压着一块谁也搬不动的石头...

每个周日的下午,顾海平都会开着他的黑色轿车,穿过半个城市,来到这家名叫“颐养天年”的私立养老院。
养老院的空气里有三种滋味:消毒水,百合花,还有一种白叟身上特有的、旧棉絮被太阳晒过又受了潮的滋味。
钱能买来周到的服务,但买不来真实上心的照料,偶然的小恩小惠,像给机器上油,能让它运转得更顺滑一些。
钟秀兰就在其间,她的轮椅停在一棵巨大的香樟树下,斑斓的阳光落在她斑白的头发和深色的衣服上。
钟秀兰的眼球缓慢地滚动了一下,像老旧座钟的指针,最终落在他脸上。她没说话。
“公司最近接了个大单子,在南边,忙得我脚不沾地。你孙子期中考试,又是全班榜首。”顾海平自顾自地说着。
他不知道除了这些还能说什么。他觉得母亲或许底子不在听,她仅仅一个需求被填充时刻的容器。
钟秀兰的嘴唇动了动,如同想说什么,但最终仅仅化成了一声细微的叹气,轻得像一片茸毛落地。
可八十岁的钟秀兰,在他兴冲冲地展现那个朝南的、带独立卫生间的大卧室时,却摇了摇头。
顾海平没办法了解。他事业有成,不缺钱,更不缺一个保姆。但他拗不过她。钟秀兰的顽固,是那种缄默沉静的、棉花相同的顽固,你一拳打曩昔,一切的力气都会被吸走,最终只能自己回收手。
所以,他为她选了全城最贵的养老院。他想,用钱总能把那点说不清的内疚感填平。
二十年曩昔,他习惯了。习惯了母亲的缄默沉静,习惯了这种程式化的探望,习惯了她仅仅一个活着的、需求他担任的符号。
养老院的护工换过几批,现在担任钟秀兰这个区的是个叫吴姐的女性,四十多岁,四肢利索,话不多。
有一次,顾海平遇见吴姐在给母亲喂饭。钟秀兰的嘴闭得很紧,像蚌壳。吴姐拿着勺子,耐心肠在外面等着,也不催。
吴姐回头看了他一眼,“老太太吃饭看心境。有时分吃得挺好,有时分一口不吃。”
吴姐顿了顿,压低声响,“顾老板,你别嫌我多嘴。老太太……如同心里有事。她不是那种老年痴呆的模糊,她是清醒的,便是不想理人。”
顾海平皱了蹙眉。心里有事?能有什么事?老公逝世得早,儿子功成名就,孙子聪明伶俐。她这一辈子,除了早年守寡辛苦了些,后来都是福分。
“里边有张旧报纸。每天下午三点,她准会拿出来,看上一个钟头。那报纸都黄得快碎了。有一次新来的小姑娘打扫卫生,想帮她把报纸收起来,她忽然就发了火,眼睛瞪得老迈,吓得那姑娘直哭。”
他有些猎奇,但也没太往心里去。白叟有点古怪,很正常。或许那张报纸上,登着父亲年轻时得过的什么奖状,或许是什么她珍爱的旧闻。
顾海平的心猛地一沉,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。他抓起衣服就往外冲,连闯了几个红灯。
钟秀兰躺在ICU里,身上插满了管子,脸上罩着呼吸机,只要监护仪上弱小跳动的曲线证明她还活着。
医师把他叫到一边,说着“器官衰竭”、“年事已高”、“做好心理上的预备”之类的词。每一个字都像钉子,敲进顾海平的耳朵里。
他开端不受操控地回想曩昔。他想起的,不是养老院里那个缄默沉静枯槁的白叟,而是几十年前的钟秀兰。
她很要强,父亲顾正祥因病逝世后,厂里人都认为她一个女性家撑不下去,她却硬是咬着牙,靠在大街工厂糊纸盒,把他拉扯大,供他读完了大学。
如同……便是从父亲逝世后。她的话渐渐的变少,笑脸也基本上没有了。搬进养老院,是最终一道闸口,完全把她关进了那个无声的国际。
这五天,顾海平推掉了一切作业,就守在病房外。他隔着玻璃看着母亲,那个他叫了六十年“妈”的女性,此时却无比生疏。
他不知道她喜爱吃什么,不知道她惧怕什么,不知道她那二十年的缄默沉静里,到底在想些什么。
“带来了,带来了。我怕她如果醒了要找。” 吴姐从一个布包里,小心谨慎地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。
那是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报纸,纸张现已黄得像秋天的枯叶,边际都起了毛。顾海平接过来,能闻到一股陈年的油墨和尘埃味。
他想翻开看看,又觉得这是窥视母亲的隐私。他犹疑了一下,仍是把报纸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里。
钟秀兰的各项目标一度很风险,医师乃至都找顾海平说话,暗示他能够预备后事了。
护理惊喜地叫来了医师。通过一番查看,医师说患者的认识有时间短康复的痕迹,但状况仍然不达观,很或许是回光返照。
顾海平冲到床边,他看见母亲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,污浊的眼球在眼眶里艰难地滚动,像是在寻觅什么。
钟秀兰的目光如同聚集在了他脸上,又如同穿过了他,看向了更远的当地。她的嘴唇翕动着,宣布一些不成调的音节。
钟秀兰的嗓子里宣布“嗬嗬”的声响,像是有一口浓痰堵着。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目光里忽然迸宣布一丝清明,但那清明里,满是惊慌和苦楚。
这几个字像针相同扎进顾海平的耳朵。他的母亲,这个与世无争、乃至有些窝囊的白叟,会对不住谁?
钟秀兰的手忽然抓紧了顾海平的臂膀,干燥的手指像铁钳相同,简直要嵌进他的肉里。
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,那目光不像是在看自己的儿子,倒像是在看一个需求防范的生疏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