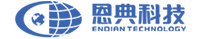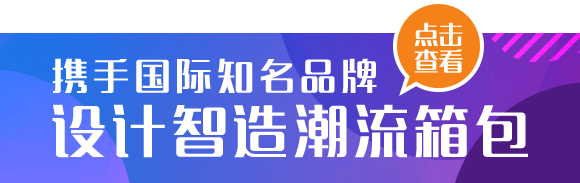【1997年8月28日,鹤岗市人民医院走廊】 “再不交费,药就要停了。”护理压低声响提示。张家几个儿女对视顷刻,谁也拿不出钱,空气像被冻住相同烦闷。
白叟名叫张国福,在矿务局火药厂干了一辈子,七十多公斤的壮实身板,现在被肺癌折磨得只剩骨头。他不喊疼,只说一句:“别给国家添麻烦。”一句话堵得儿女落泪,却也无人再敢提出院。
债台已高,房子早卖,亲朋能借的都借遍。院方几回账单下发,底线再明晰不过:欠费停药。小女儿遽然想起父亲偶然说过“当过兵”,她翻出尘封已久的黄布包,在一张褪色的复员证上看到“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”字样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思,她拨通当年团部留下的号码。
电话那头明显也愣住了,随后只说一句:“请必须原地等候。”两天后,一辆军牌救护车迅雷不及掩耳抵达鹤岗。随车医师直接为白叟处理转院手续,目的地:北京总医院。当地医院才知道,手里的一般病历背面,竟是一位两次特等功获得者。院长连连自责:“真不知道他是那样的英豪。”

抵京第三天,专家会诊给出成果——右肺大面积实变,癌灶分散,战时旧伤让医治难上加难。院里给他换上特护病房,却没人听到白叟叫苦,偶然清醒时,他只重复吩咐:“费用别超标准,国家的钱要花在刀刃上。”
故事由此回溯到1931年。吉林榆树县的寒夜里,刚刚出世的张国富被放进旧棉被,爸爸妈妈叹口气便去地主家干活。十几岁,他就像牲口相同给地主放牛、掏粪。靠吃剩饭熬日子,让他早早懂得一个道理:贫民不翻身,就永久抬不起头。
1946年春,他趁夜色逃离地主宅院,直奔邻近的东北民主联军招兵点。十五岁的少年递上姓名时,骨节由于激动而发白。练习场上,他分外拼命,刺杀、投弹、射击样样争榜首。老兵看不惯他的小身板,戏弄:“小孩,扛得动枪吗?”他答:“我能扛着仇视。”

不到一年,他随部队攻江密峰。第9团连连受阻,前方指挥所里,三名营连主官倒在血泊。张国富趴在满是弹片的山坡,探索出一条死角小沟,硬是在炮火停歇间爬至敌军中心。掷出三颗手榴弹后,他高喊“缴枪不杀”,竟让整座碉堡哑火,一名中将官佐举手屈服。事后军报头版点评:一人扭转局势。那年,他十六岁。
辽沈战役迸发,他再次被编进纵深交叉部队。黑山阻击战,敌坦克尖啸着冲阵,他挂彩倒地却装死,等对方换防时滚入指挥部,反手锁住参谋长脖颈,逼其命令全线撤离。此举被定为特等功。
1950年榜首届全国战斗英豪代表会,他挤进78名特等功队伍。大会后,他受邀同主席、总理共进家宴。饭桌粗陋,主席却亲身给他夹菜,问:“小,本年多大?”“十九岁。”主席笑道:“好,好,好。”三个“好”,全场拍手。

国家正待建造,他原可安心留守后方。抗美援朝炮火点着,他自动递送请战书,理由只要一句:“枪还响,血未凉。”在朝鲜345.6高地,他带领一个连守住阵地七昼夜。棉衣棉絮煮水果腹、皮带当干粮,最终只剩他一人压着扳机。救护人赶届时,他胸骨碎裂,右腿折断,却还紧握步枪。
几年之后,军校进修期间,他却要求复员。“国家需求文化人指挥,我不识字,留队反而拖后腿。”领导款留,他摇头。复员证办妥,他又改了一个字,把“富”写成“福”,不想再被光环捆绑。
1960年代,他随招工大潮去了黑龙江鹤岗。单位组织他当消防员,后来又调火药厂。高爆粉尘、硝烟味随同三十年,他从不请求劳保补助,也从不提战功。车间新工人只当他是个缄默沉静老班长,没人知道背面那段刀口舔血的年月。

因而,1997年的那场催费风云才分外刺目。若非女儿翻出复员证,他可能在县城医院静静停药,静静离世。北京医治期间,原47军老首长来看望,他身体虚弱,仍举手敬礼。首长问:“有什么想要的?”他吃力答复:“期望党和国家好。”整屋人鼻头发酸,却无人落泪,由于他最厌烦脆弱的眼泪。
1998年春,张国福病情恶化。清晨,他对床旁的老军医轻声说:“谨记节省。”随后呼吸渐止,终年六十七岁。当天,总政发来讣电,以“志愿军特等功臣”称号这位回绝鲜花和掌声的白叟。

有人说,日子把英豪磨成俗人;也有人说,英豪甘心把自己偿还日子。张国福的挑选或许最难——既不张扬,也不躲避,用静静无闻的四十年,看护了战争年代许下的许诺:让女性孩子在平和中睡好觉。
这位白叟走了,留下一句朴素嘱托,也留下一个最顽强的背影。当年那张染着硝烟味的复员证,现在被子女装进相框挂在墙上,和他生前的工牌并排。两张证件,一张写着血火,一张写着汗水,却都是同一个姓名——张国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