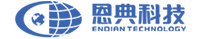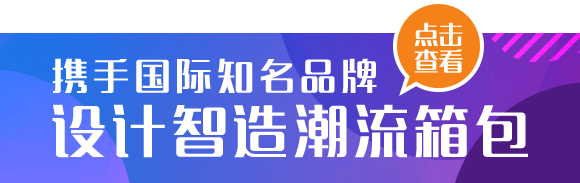动身前三天,刘子龙在油灯下缝制担子内衬。他取出一块特别的蓝棉布——那是许昌党安排专用的暗号布料,靛青根柢上织着极细的银线,在月光下会泛出弱小的星芒。他将布缝进担子夹层,线头成心留出三寸长,若有人动过手脚,一望即知。又在布角绣了朵极小的野菊,针脚细密,是董秀芝手把手教他的:“花瓣要向右旋,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。”她其时笑着说,“如果出事,我认得你的记号。”
他还把家里的柴刀磨得雪亮,刃口映着灯影,寒光如水。刀藏在担子夹层的暗格里,用油纸裹了三层。又托谢文豪悄然联络了几个信得过的后生,约定在徐州郊外三十里的山神庙接应:“要是货有问题,就着手抢。宁可毁了,也不能让它流出去害人。”

第一次随朱鲁岭出门时,麦子刚打完场,郊野空阔,风卷起金黄的麦茬,像大地褪下的旧衣。刘子龙挑着个空担子,里边藏着那把磨尖利的柴刀,肩头压得生疼,却走得稳如磐石。
火车在黑夜里穿行,铁轨宣布烦闷的轰鸣。朱鲁岭的货箱被帆布盖得严实,缝隙里漏出一股甜腻的香气,不似茶叶的贫苦,倒像谢俊当年在洛阳码头走私的烟土——那种混着罂粟与腐朽果肉的气味,令人作呕又昏眩。
刘子龙托言解手,绕到卡车车厢后。借着月光,他看见箱角印着“奉天制药株式会社”的字样——上一年在壮丁队见过,那是日军以“药品”为名走私的幌子,专供华北沦陷区毒化大众。
“这是啥?”在徐州车站转车时,刘子龙遽然按住朱鲁岭的货箱。箱子晃动时宣布细碎的沙沙声,绝不是绸缎或药材该有的动态。他成心打翻桌上的茶水,水顺着箱缝渗进去,很快洇出一片深色,模糊显出日文标识:“阿片精製”。
朱鲁岭的脸色变了变,敏捷掏出一块银元塞进他手里,声响压得极低:“兄弟莫问那么多,到当地就知道了。”他的指尖冰凉,目光躲闪,“这世风,想做点事哪能洁净?等我们攒够了钱,拉部队抗日,谁还会提这些?”
刘子龙把银元攥在手心,边际硌得掌心生疼。他泰然自若地摸了摸担子内侧的蓝棉布——线头还在,未被牵动。车窗外闪过一块路牌:“距商丘还有三十里”。他心头一紧:张本曾说过,商丘是日军在豫东最大的中转站,设有隐秘库房。难不成……这批货是要运往那里?
他悄然把柴刀往腰后挪了挪,指尖无意触到棉布下缝着的一小片红绒布——那是1927年雪夜中那枚血染红五星的残片。七年曩昔,色彩已褪成暗褐,却仍如烙铁般烫着他的心口。
他心中策画:若能截下这批货,不仅能救下李家婶子——她儿子因啃咬卖田卖房,最终吊死在槐树上;那价值恐怕不止五百大洋!满足装备一支二十人的小队,乃至能在拐河村办个药铺,免费给贫病同乡抓药。
第2次运送时,刘子龙成心掉队,绕到卡车必经的山神庙。他在神像后藏了块木牌,用炭笔写着“烟土过境”,周围画了个指向商丘的箭头——那是给或许路过的游击队留的信号。他还用指甲在庙柱上刻了“龙”字暗记,只需安排内部人才懂其意。
回来途中,他远远看见朱鲁岭的一个侍从正蹲在自己的担子旁,手指在缝线处探索。刘子龙心头冷笑:狐狸尾巴总算显露来了。但他面上泰然自若,只当没看见。
徐州车站人声鼎沸,小贩叫卖,旅客喧闹。遽然,一群路警如狼如虎冲来,刺刀寒光一闪,挑开朱鲁岭货箱上的帆布。刘子龙瞳孔骤缩——那些用油纸包着的东西,一块块黑褐色,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甜香,正是膏!
他下意识摸向担子内侧——蓝棉布的线头断了,明显被人动过手脚。朱鲁岭早已与间谍串通好,只需缠住刘子龙顷刻,自己便可抽身。他撒腿就跑,身影瞬间消失在熙攘人群中。
刘子龙的手天性地摸向担子底下的柴刀,却见警徽在灯光下闪着寒光,像极了当年郏县监狱的铁窗。他遽然理解:自己毕竟仍是踩进了圈套。朱鲁岭底子不是什么“爱国商人”,而是借抗日之名行贩毒之实的汉奸走狗!
可怀里的蓝棉布还在,红星的残片硌着心口,像在说:不能就这么认栽。为了同乡,为了安排,这一步,他不能退。
奋斗中,他瞅准时机撞翻一个军警,趁乱掏出怀里的二十响驳壳枪。子弹擦着一名间谍的耳朵飞过,钉入木柱,溅起木屑。但更多军警蜂拥而至,棍棒如雨,他终被死死压在地上,双手反剪,铐上铁镣。
徐州陆军监狱的铁门关上时,麦收的时节早已曩昔。牢房阴冷湿润,墙角霉斑如地图,铁窗外偶然传来乌鸦的嘶鸣。刘子龙望着头顶那方小小的铁窗,想起冢头乡翻滚的麦浪,想起董秀芝站在田埂上朝他挥手的身影,裙裾被风吹得鼓胀如帆。
朱鲁岭没被抓到,传闻跑回了武汉,持续做他的“生意”。而他这个“从犯”,因“走私违禁品”,被判了两年徒刑。
狱友里有个参与过长城抗战的老兵,左腿齐膝而断,总爱讲喜峰口大刀队夜袭日军的故事。“鬼子的三八大盖再凶猛,也挡不住咱中国人抱团。”老兵的断腿在阴雨天疼得直哼哼,却总往刘子龙手里塞半截烟卷,“等出去了,找支真抗日的部队,比啥都强。别跟那些假抗日、真发财的混蛋搅和!”
1938年春天来得分外早。一月二十那天,牢房遽然炸开锅——日军迫临徐州,守军败退,监狱紧迫分散,提早开释一批“轻刑犯”。
刘子龙走出监狱大门时,晨光熹微,薄雾如纱。他眯起眼,看见董秀芝站在路旁的老槐树下,怀里抱着云中。孩子看见他就喊“爹”,声响脆得像新抽的柳芽,带着泥土与阳光的滋味。
“回家。”董秀芝的眼睛红了,却笑着帮他理了理乱发,指尖拂过他额角的旧疤,“冢头乡的麦子快熟了,拐河村的地还等着我们种呢。”她往他手里塞了个布包,翻开一看——正是那片蓝棉布,野菊图画上,她又用红线绣了个小小的“安”字,针脚温顺,似乎在说:安全归来,就是成功。
拐河王村的老槐树抽出新芽时,刘子龙扛着锄头走进自家的地。土地仍是那么扎实,踩上去能够感觉到脉息般的跳动,似乎大地也在呼吸。董秀芝在宅院里晒着新收的芝麻叶,香气飘出老远。云中拿着根木棍在地上划,嘴里喊着“杀鬼子”,那仔细的容貌,像极了当年的武凤翔。
夜里,他坐在老槐树下,听着远处传来的风声。董秀芝端来一碗热姜汤,轻声说:“要不是上一年武凤翔和谢文甫拉起了几十人的部队,日夜巡查,捍卫着家乡,不知道村上又被土匪侵害过几回了。”她顿了顿,目光坚决,“你回来了,能够一同干。早晚会找到安排的。”
远处的天际线泛起微光,像极了那年从郏县监狱出来时,董秀芝站着的方向。他摸了摸怀里的蓝棉布,遽然觉得,就算走了岔道,只需根还扎在这片土地上,只需心中那团为同乡、为民族、为崇奉而燃的火不灭,总有时机从头找到方向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