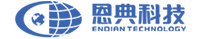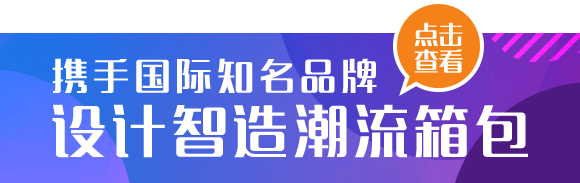创造声明:本文为虚拟创造,请勿与实际相关本文所用资料源于互联网,部分图片非实在图画,仅用于叙事出现,请知悉
“三娘,一个女性家,笑得这么美观做什么?”邻桌王婆子古里古怪的话像根针,扎得柳三娘脸上的笑意僵了半瞬。
她不知道,自己为生计强撑出的笑脸,在旁人眼中,早已成了某种不洁白的依据。

清河镇的午后,总是带着点无精打采的劲儿。阳光穿过老槐树的叶隙,在青石板路上洒下碎金,熏得人昏昏欲睡。可镇东头的“半日闲”茶馆里,却是一片如火如荼。
平话先生正讲到武松打虎的紧要关头,惊堂木“啪”地一响,合座的茶客齐齐叫了声“好!”,铜钱叮叮当当落进先生跟前的铜盘里,混杂着瓜子壳洪亮的碎裂声,茶碗磕碰的叮当声,构成了一曲独归于贩子的热烈交响。
在这片喧哗声中,一个青色的身影如游鱼般灵敏络绎。她便是这茶馆的主人,柳三娘。
柳三娘本年不过二十有四,身上穿戴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青布衫子,腰间拿一条洁净的布围裙系着,勾勒出不盈一握的腰身。她长得不算顶美,却是那种耐看的娟秀,一张鹅蛋脸,肤色是终年劳累养出的麦色,一双眼睛特别亮,像是两泓秋水,寂静得不像她这个年岁该有的容貌。
她四肢利索得很,左手拎着大铜壶,右手稳稳地托着几只茶碗,膀子上还搭着条擦桌子的布巾,一路走曩昔,给这个添水,给那个续茶,嘴里还应着客人的玩笑话,脸上挂着得当又不过火热络的笑脸。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沾湿,贴在光亮的丰满的额头上,她也顾不上去擦。
这家“半日闲”茶馆,是柳三娘的安居乐业之所,也是她和五岁儿子小石头的悉数依托。
说起来,柳三娘的命不算好。她本是邻村的姑娘,十七岁那年嫁给了镇上的木匠张大郎。张大郎是个厚道本分的手艺人,人高马大,待柳三娘是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夫妻俩一条心,起早贪黑地干活,攒下些积储,又跟亲属借了点,才盘下这个小茶馆。眼瞅着儿子小石头一天天长大,日子像那新发的面团相同,眼看就要蒸发起来,可老天爷却开了个顶大的玩笑。
两年前,张大郎跟人上山砍木,遇上了山体滑坡,人就那么没了。噩耗传来,柳三娘当场就晕死曩昔。醒来后,她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,哭了三天三夜,眼泪都流干了。娘家劝她,趁着年青,带着孩子改嫁算了。婆家虽不舍,但也知道孤儿寡母的日子难熬。
可柳三娘骨子里有股倔劲儿。她没回娘家,也没改嫁。她对一切人说,这是她和她男人的汗水,她要守着。她把一切的沉痛都咽进了肚子里,一个人,硬生生地把这家茶馆撑了下来。镇上的街坊邻里,提起柳三娘,多是叹一声“不简单”,夹杂着几分怜惜与敬仰。
就在这茶馆生意最忙的时分,一个不那么调和的身影从门口晃了进来。来人二十出面,身形瘦长,穿戴一身不甚洁净的直裰,脸上带着一股子圆滑气,正是柳三娘的亡夫的弟弟,张二郎。
张二郎自打哥哥逝世后,就没少往茶馆跑。他一不干活,二不帮助,纯粹是来闲逛的。他一进门,就跟进了自己家相同,熟门熟路地绕过客人,径自走到货台后头。
“嫂子,生意不错啊。”他斜倚在货台上,一双滴溜乱转的眼睛往钱匣子里瞟,“看来大哥留下的这点家当,被你运营得绘声绘色嘛。”
这话听着像是夸奖,可那酸溜溜的调子,任谁都听得出里边的眼红和不甘。柳三娘正垂头找茶叶,闻言动作顿了一下,她抬起头,脸上仍旧挂着笑,仅仅那笑意未达眼底:“二郎来了,自己找当地坐吧,嫂子这儿忙着呢。”
“不坐了,不坐了。”张二郎摆摆手,嘿嘿一笑,搓着手说,“我便是来看看。对了嫂子,小石头那孩子,是不是该添两件新衣裳了?天儿眼瞅着要转凉了。我这个当叔叔的,看着也疼爱。”
柳三娘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知道他又要来那套了。她停下手里的活计,看着他,声响有些发沉:“孩子衣裳够穿,不劳你想念。”
“哎,话不能这么说。我哥就留下这么一根独苗,我这当叔的能不想念?”张二郎说着,竟是自己着手,拉开了钱匣子,从里边捻出几串铜钱,在手里掂了掂,“我先拿去给孩子扯几尺布,剩余的,就当是……当是我先跟嫂子借的,回头手头宽余了就还。”
他说得振振有词,动作更是行云流水,明显不是第一次了。柳三娘气得胸口发堵,可看着他那副无赖相,又看看合座的客人,终究是没发生。
她不能在揭露场合之下跟小叔子闹翻,那只会让人看笑话。她只能死死咬着后槽牙,看着张二郎把钱塞进怀里,吹着口哨,大模大样地走了出去。
那背影消失在门口,柳三娘才泄了气似的,扶着货台喘了口气。她眼圈悄悄泛红,心里说不出的憋屈和厌烦。
“这张家二郎,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,三天两头来抽丰,吃绝户呢!”一个姓李的老汉往地上啐了一口。
“可不是嘛,三娘一个女性家,拉扯着孩子,撑着这么个铺子,多不简单。这小叔子倒好,一点忙不帮,还净来添堵。”周围一个王大爷赞同道,不住地摇头。
“要我说啊,”一个刚从外地回来的货郎,呷了口茶,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,“这女性家,仍是得有个男人支持。特别是三娘这样的,年青貌美,又是自己当家做主,外面盯着的人能少了?对错也多。”
话题一转,这货郎像是想起了什么风趣的事,眼睛一亮,声响压得更低了:“说起这女性的事儿,我可跟你们说个稀罕的。我前阵子在邻县贩货,听闻那儿有个叫陈瞎子的相士,那叫一个神!别管那女性心里藏得多深,多会装,他底子不必旁证,也不必探问,就这么当面瞧一眼,只瞧她那眼角,就知道她心里头,究竟有没有藏着野男人!”
这话一出,本来喧哗的茶馆里,竟有顷刻的安静。几个竖着耳朵听的茶客都来了兴致。
“千真万确!”货郎拍着胸脯确保,“人家说了,女性那眼角啊,门路多着呢!要是心里洁净,守着本分,那眼角的纹理,就算有,也是清清爽爽,顺着一个方向走。可要是动了其他心思,那纹理就不相同了,会散乱,会分叉,叫什么‘桃斑纹’。要是跟人有了苟且,那纹理深处还会带上水光,叫‘泪子纹’。听说啊,这陈瞎子看这个,分毫不差!多少家里男人置疑自家婆娘不洁净,闹得翻天覆地,终究请陈瞎子去看一眼,是真是假,当场就理解了!”
这番话说得神乎其神,茶馆里的气氛登时变得有些奇妙。几个茶客的目光,像是不受操控似的,不谋而合地,悄悄地,飘向了正在货台边垂头算账的柳三娘身上。
柳三娘正专注拨着算盘珠子,浑然不觉自己成了世人视野的焦点。但那几句“桃斑纹”、“泪子纹”的话,仍是像茸毛似的,悄悄搔过她的耳朵。她皱了蹙眉,心里有些不舒服,只觉得是些无聊的乡野风闻,无稽之谈。她站启航,端起茶壶又去给客人添水,将那些闲言碎语甩在了死后。
仅仅,“看眼角纹理识女性心”这句话,却像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子,被风吹进了世人的心湖里,漾开了一圈看不见的涟漪。
黄昏时分,落日的余晖给茶馆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色。茶客们陆陆续续散了,热烈了一天的“半日闲”总算安静下来。柳三娘打发了店员回家,自己开端拾掇终究的杯盘。
这时,门口的风铃“叮铃”一响,走进来一个青衫年青人。他叫徐进,是个预备本年秋试的秀才,家境不算好,住在镇子西头的一间旧屋里。他素日里最喜欢来这“半日闲”,点上一壶最廉价的粗茶,就能安安静静地坐上一下午,读他的圣贤书。
徐秀才人如其名,文质彬彬,说话总是轻声细语。他见柳三娘一个人辛苦,有时会自动帮她算算账,核对一下当日的流水,或许教她那调皮的儿子小石头认几个字。柳三娘对他,是心存感谢的。
“徐秀才来了,快坐。”柳三娘抬起头,脸上显露一丝疲乏却真挚的浅笑,“这就拾掇完了。”
“我不是来喝茶的。”徐进从随身的布袋里,小心谨慎地拿出一册线装书,册页由于翻阅的次数多了,边角有些卷起。他略带羞赧地递曩昔,“这是我闲时抄写的一些前人诗集,里边有些语句较为风趣,想着三娘你闲暇时也爱看几页闲书,便……便送给你解排遣。”
柳三娘愣了一下,急速摆手:“这怎样使得?徐秀才你读书要紧,这都是费工夫的活儿。”
“不妨的,抄书也能温故知新。”徐进坚持着,将书塞到她手里,“三娘素日多有照顾,我一个穷书生,也没什么好谢的,就当是……就当是还你那几壶茶钱吧。”
他的话说得诚恳,柳三娘也不好再推托。她垂头翻开书册,只见里边的笔迹隽秀整齐,墨香扑鼻。她翻到一页,看到一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起浮月黄昏”,不由得轻声念了出来。徐进在一旁轻声解说了这句诗的意境。柳三娘听着,好像看到了那月下的梅花,闻到了那清凉的香气,一天的疲乏和愁闷都消散了不少。
她又往后翻,看到一句玩笑的歪诗,不由得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。这一笑,是发自心里的,卸下了一切防范和假装。她眉眼弯弯,像一轮新月,眼角那几道因终年劳累和忧思而生出的细纹,也在这笑脸里纵情地舒展开来,非但不显老态,反而添了几分生动和妩媚。
两人就站在货台边,就着从窗户透进来的终究一抹天光,轻声交谈着,气氛安静而夸姣。
仅仅他们谁也没注意到,一个身影在茶馆门口停了顷刻。那是刚串完门预备回家的王婆子,镇上有名的长舌妇。她本是无意一瞥,却正美观见灯下相谈甚欢的两人,特别是柳三娘那笑得畅怀的容貌。
王婆子停下脚步,眯起一双精明的小眼睛,视野牢牢地锁在柳三娘的脸上,精确地说,是锁在她那因笑脸而变得分外明晰的眼角上。
她想起下午在茶馆里听到的那个风闻,嘴巴撇了撇,嗓子里宣布一声意味深长的冷哼,随即回身,扭着腰,箭步走进了周围黑漆漆的巷子里。
柳三娘对此一窍不通。她感谢地收下了诗集,送走了徐秀才。夜深人静,她哄睡了儿子小石头,点亮了桌上的油灯。她拿出那本诗集,又不由得翻看起来。看着看着,她鬼使神差地取过一旁的小铜镜,凑到灯下,细心打量着镜中的自己。
镜子里的女性,面带倦容,但端倪仍然明亮清明。她的手指,无意识地,悄悄抚过自己的眼角。便是这儿,这几道细纹。
它们是为亡夫熬干了眼泪留下的,是为生计起早贪黑刻下的,是为拉扯儿子长大成人愁出来的……它们是她这几年一切辛苦的见证。
一丝她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,像初春的藤蔓,悄然无声地,开端在她的心底延伸开来。
清河镇的清晨,是从井边的喧哗开端的。妇人们拎着木桶,围在井台边,一边浣洗衣物,一边交换着镇上最新的音讯。这音讯,有时分比井水还要清冽提神。
王婆子今日便是这井台边的中心。她一边用木棒“砰砰”地捶打着盆里的衣裳,水花四溅,一边压低了声响,对着周围熟悉的李家婶子“咬耳朵”:
“我昨儿个黄昏亲眼看见的!”王婆子说得唾沫横飞,好像自己抓住了什么惊天的大隐秘,“她跟那个徐秀才,便是那个穷秀才,在茶馆里头,挨得那个近哦!两人头都快凑到一块儿去了!那柳三娘,笑得那叫一个花枝招展,眼角的纹理都舒展开了,跟朵花儿似的!啧啧,你瞧瞧,一个寡妇家,成天跟个年青后生暗送秋波的,像啥样子?她还当自己是大姑娘呢?也不想想她男人那坟头的草,都多高了!”
这话就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,一传十,十传百,版别也随之升级换代,越来越离谱。
卖猪肉的屠夫老李,掂着明晃晃的屠刀,冲她嘿嘿直笑,嗓门洪亮:“三娘,今儿个要几斤肉?看你最近这气色,红光满面的,是否有什么大喜事啊?要是有,可别忘了给街坊邻里发喜糖啊!”
他这话一出口,周围买菜卖菜的人都跟着一阵哄笑。那笑声里,带着点含糊,带着点看热烈不嫌事大的促狭。
柳三娘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就红了,像是被人当众剥了一层皮。她想说些什么,可嘴巴张了张,却发现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在这么多双眼睛的凝视下,任何解说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她只能仓促丢下几个铜板,抓起案板上的肉,难堪地挤出了人群。
以往那些爱跟她拉家常的老茶客,今日见了她,目光都有些躲躲闪闪。有的人跟她说话,目光总是不自觉地往她脸上,特别是眼角瞟。她给客人添水,那客人竟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,好像她是什麽不洁净的东西。

更有几个素日里就不务正业的年青混混,更是肆无忌惮。他们要了一壶最廉价的茶,却不喝,就坐在角落里,用那种黏膩的、让人厌恶的目光,在她身上来回地扫。
“嘿,你看三娘这腰身,这脸蛋,哪里像个守了两年寡的?我看啊,比那有男人的婆娘还润泽呢!”
污言秽语像苍蝇相同嗡嗡作响,柳三娘气得浑身发抖,恨不能将手里的滚水茶壶直接泼曩昔。可她不能。她是一个开门经商的,和气生财,开罪了客人,这茶馆还怎样开下去?她只能假装没听见,回身走进后厨,眼泪却不争光地在眼眶里打转。
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,张二郎,更是乐见其成。他在酒馆里跟一帮狐朋狗友喝酒,听着外面传得沸反盈天的闲话,更是满意地添枝加叶。
他一拍桌子,喝得满脸通红:“我早就看出来了!我那嫂子就不是个省油的灯!你们想想,她一个女性家,能有这么大本事,把茶馆撑得风生水起?背面没男人帮衬着,鬼才信!我大哥才走了两年,尸骨未寒呐!她就这么迫不及不及待地想找下家,还想把咱们张家的家产,拱手送给外姓人!我告知你们,只需我张二郎还有一口气在,就绝不能让她达到目的!”
他一番话说得理直气壮,好像自己才是那个保卫宗族荣誉的英豪。他把自己那点贪婪和觊觎,奇妙地包装成了对亡兄的忠实和对宗族的职责。
柳三娘从开端的困惑和委屈,渐渐变成了愤恨和无力。她想不理解,自己日夜劳累,循规蹈矩,没偷没抢,没招谁没惹谁,为何要无缘无故地受这般诬蔑?
有一次,她在巷口听到两个妇人正唾沫横飞地谈论她,说她“那眼角的纹理都散开了,一看便是心思活络,水性杨花”,她气得浑身颤抖,想也没想就冲了上去:“你们胡言乱语些什么!”
那两个妇人吓了一跳,见是正主来了,脸上闪过一丝为难,随即又梗着脖子嘴硬:“咱们说啥了?咱们说啥了?说你两句还不行了?”说完,两人讪笑着,脚底抹油似的溜走了。
柳三娘站在原地,像一拳重重地打在了棉花上,满腔的怒火和委屈无处宣泄,堵在胸口,简直要让她窒息。
渐渐地,她开端变得灵敏多疑。她不敢再跟徐秀才多说一句话,乃至在茶馆里看到他,都会下意识地避开。她不敢笑了,生怕一笑起来,眼角的纹理就会成为他人嘴里新的依据。
夜里,她辗转反侧地睡不着。黑私自,她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指抚摸自己的脸。镜子里的自己,由于长时刻的焦虑和失眠,眼圈发黑,脸色瘦弱,眼角那几道细纹,好像真的比曾经更深、更乱了。她乃至开端含糊地置疑自己:莫非我真的有啥当地做得不对吗?是不是我出头露面地经商,本便是一种错?
就在柳三娘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时分,张二郎觉得时机成熟了。他再次登门,脸上挂着假惺惺的笑脸。
“嫂子,最近挺累的吧?”他一坐在椅子上,翘起了二郎腿,“你也听见外面的风言風语了。说实话,这些话实在是不好听,不但对你名声不好,对咱们张家的名声,也不好啊。”
他顿了顿,图穷匕见:“所以我想了想,不如这样。这茶馆,你一个女性家也别料理了,就交给我来管。我呢,好歹是张家的人,理直气壮。我确保,每个月准时给你和小石头满足的生活费,绝饿不着你们娘俩。这样一来,你也能在后宅院个清净,省得在外面出头露面,惹人闲话。你看,我这是为你考虑啊,嫂子。”
柳三娘看着他那张写满了估计的脸,心头燃起一股冷冷的火焰。她总算理解,前面一切的谣言蜚语,都不过是为此时的图穷匕见做衬托。
“你休想。”她站直了身子,目光坚决而严寒地看着他,“这茶馆是我和大哥的汗水,是我和小石头的命根子。只需我柳三娘还有一口气在,你就别想打它的主见。”
秋意渐浓,宅院里的老槐树叶子开端泛黄。清河镇的这场风云,非但没有停息,反而在张二郎的故意推进下,愈演愈烈。柳三娘的日子,就像这气候相同,一日比一日凉。
这日午后,茶馆里客人不多。柳三娘正教着小石头描红,门口的风铃又响了。她昂首一看,竟是徐进。他穿戴一身洗得洁净的旧儒衫,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行囊,看样子是要出远门。
自打谣言起来后,徐进为了避嫌,现已良久没来过茶馆了。今日忽然到访,让柳三娘有些措手不及。
“三娘。”徐进的脸上带着愧疚和不安,他走到货台前,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小包,放在桌上,推到柳三娘面前。
“我明日就要启航去府城参与秋试了,此去经年,不知何时才干回来。”他声响很低,却很明晰,“近来镇上的一些闲言碎语,我也听说了。皆因徐某而起,给你平添了这许多费事,我……我心中有愧。”
他翻开布包,里边是几块碎银子,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。“这点银子不多,是我素日节衣缩食攒下的。你拿着,以备不时之需。我知道你不易,若……若将来遇到什么难处,或许能应个急。”
他看着她,目光明澈而真挚:“三嫂,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你莫要将那污言秽语放在心上。”
柳三娘看着桌上的银子,又看看徐进那张写满关心的脸,鼻子一酸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在这段被全世界孤立和误解的日子里,这是她听过的仅有一句暖心话。可她怎样能要他的钱?一个穷书生,赶考的旅费都未必凑得齐。
“不,徐秀才,我不能要!”她急速把银子推回去,“你的心意我领了,这钱你快收好,赶考路上处处都要花钱……”

张二郎像一头被完全激怒的公牛,从街角猛地冲了进来。他双眼赤红,死死地盯着桌上的银子和两人推搡的手,脸上是抓到现行的狂喜和狰狞。
他一个箭步冲上前,大手一挥,“啪”的一声,将徐进手里的银子全都打翻在地!碎银子叮叮当当地滚了一地。
“光天化日之下,你们就敢在这儿拉拉扯扯,送银子!这是什么?这便是的依据!”他伸出手指,简直要戳到柳三娘的鼻子上,破口大骂,“我大哥尸骨未寒!你这个不要脸的女性,就敢这么明火执仗地给他戴绿帽子!咱们张家的脸,都被你丢尽了!”
仅有的几个茶客,连同听到动态的路人,全都“呼啦”一下围了过来,把小小的茶馆门口堵得风雨不透。
柳三娘的脸,由红转白,又由白转青,浑身的血液好像一会儿都涌上了头顶。她气得浑身发抖,胸口剧烈地起伏着。这些日子积累的一切委屈、愤恨、侮辱,在这一刻完全爆发了!
她猛地抓起货台上那把沉重的黄杨木算盘,竭尽全身力气,朝着张二郎的脸就砸了曩昔!
“张二郎!你血口喷人!”她尖声嘶吼,声响都变了调,“我柳三娘行得正坐得端,六合可鉴!你少在这儿撒泼耍混,污我名节!”
张二郎吓了一跳,随即愈加暴怒。徐进一个文弱书生,也被这出人意料的变故气得满脸通红,他挡在柳三娘身前,对着张二郎大声呵斥:“你……你简直是无理取闹!含血喷人!”
“哟呵!还护上了!”张二郎见状,非但不惧,反而愈加满意。他一把推开徐进,指着他对围观的世人大声嚷嚷:“大伙儿都看看!都来评评理!这野男人还知道护着她呢!我说错了吗?人赃并获!这茶馆是我张家的工业,我大哥留给我侄儿的!轮得到她一个外人,勾搭着野男人,想把咱们张家的家产都给损坏了吗?”
“看这姿势,不像假的啊……”“这徐秀才平常看着挺文雅的,怎样也……”“寡妇门前对错多,这话一点不假。”
柳三娘的哭喊声,张二郎的叫骂声,徐进苍白的辩解声,还有围观大众那一句句诛心的谈论声,交错在一起,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将柳三娘死死地困在中心。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,简直要站立不住。
紊乱中,张二郎带来的一个狐朋狗友,素日里就愛出馊主见的刘三,眼球子一转,大声喊道:“已然说得这么热烈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谁也压服不了谁,不如找个能断对错的人来断断!”
张二郎马上抓住了这个话头,他眼中闪烁着狠毒而振奋的光辉。他要的便是这个作用,把工作闹大,闹到无法收场,他才有时机趁火打劫。
“对!说得好!我早就听说了,城东住着个陈瞎子,看相最是灵验!特别是看女性!他只需一瞧女性眼角的纹理,就知道她安不安分,守不守妇道!”
他环顾四周,用最具鼓动性的口气高喊:“柳三娘!你已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洁白,说自己委屈!那你敢不敢,现在就当着全镇街坊邻居的面,让陈瞎子给你瞧瞧?!”
他提高了音量,简直是在吼怒:“大伙儿说,这个法子公不公平?她要是心里没鬼,身正不怕影子斜,就没什么不敢的!要是她敢去,陈瞎子说她洁白,我张二郎当场给她磕头认错!可她要是不敢去……哼哼,那是啥意思,就不必我多说了吧!”
“对!去让陈瞎子看看!”“这个法子好!是骡子是马,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!”“不敢去便是心虚!”
柳三娘瞬间如坠冰窟。她浑身严寒,血液都好像凝结了。她知道,这是一个早就为她设好的,最狠毒的骗局。
去?那个素未谋面的陈瞎子,万一和张二郎是一伙的,或许信口胡说,那她这辈子就完全完了,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不去?在一切人的眼中,那就等同于默认了自己有鬼,坐实了这“不守妇道”的罪名。
她失望地看着周围,看到的是一张张或猎奇,或麻痹,或幸災樂禍,或等着看好戏的脸。没有一张脸是为她说话的。她像一个被狼群围住的猎物,退无可退。
时刻好像在这一刻被拉得极长,茶馆门口的空气凝滞得让人喘不过气。一切的目光都聚集在柳三娘惨白的脸上,等着她的答复。
“怎样?不敢了?”张二郎脸上挂着胜利在望的狞笑,步步紧逼,“方才拿算盘砸我的那股劲儿呢?你不是说自己行得正坐得端吗?那就去啊!”
柳三娘的身体在悄悄颤抖,她的手死死地攥着衣角,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的肉里,带来一丝尖利的刺痛,才让她没有当场倒下去。她抬起头,目光扫过那些起哄的、冷酷的、看热烈的面孔,心里一片冰凉。
她知道,她现已没有退路了。今日若是不去,她和儿子的名声就完全毁了,这茶馆也再开不下去。反正都是死,不如去赌那终究一线生机。
“好!有胆色!”张二郎振奋地一挥手,“大伙儿都做个见证!咱们现在就去城东,找陈瞎子!”
张二郎昂首阔步地走在最前面,像个取胜的将军。柳三娘被威胁在人群中心,死后是黑压壓的人群,像一条移动的河流,声势赫赫地朝着城东的方向涌去。这不像去算命,更像是一场揭露的审判和游街。
柳三娘低着头,长长的睫毛垂下,遮住了眼里的一切心情。她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,只能盯着自己脚下的青石板路,一步,一步,机械地往前走。每一步,都像是踩在烧红的刀尖上,疼得钻心。周围的指指点点和交头接耳,像很多根看不见的针,扎在她身上,让她皮开肉绽。
“嫂子!三娘!”徐进的声响在人群外围响起。他一个文弱书生,被几个无赖无赖有意无意地拦着,底子挤不进来。他们推搡着他,嘴里不干不净地嘲讽:“哟,奸夫还想护着呢?你仍是省省吧!”“再往前凑,留神你的狗腿!”
徐进急得满头大汗,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柳三娘那单薄的身影,被汹涌的人潮吞没,渐行渐远。他心中充满了无力和自责,拳头握得发白。
城东的巷子,比镇中心要清静许多。陈瞎子的住处,就在一条窄巷的止境,是个看起来有些年初的寒酸小院。院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,院门是两扇斑斓的木板门。
张二郎粗鲁地推开院门,一群人“呼啦”一下涌了进去。宅院里不大,角落里用竹竿暴晒着一些草药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墨香和淡淡的药味混合在一起的独特气味,让喧嚣的人群都情不自禁地安静了几分。
他穿戴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衫,头发斑白,在脑后束成一个髻,身形干瘦,脊背却挺得垂直。他好像没有听见宅院里的喧哗,一动不动,像一尊入定的雕像。
世人这才看清他的容貌。他约莫六十来岁,脸上布满了深入的皱纹,下巴上藏着一小撮山羊胡。最众所周知的,是他那双眼睛。那是一双灰白色的、肯定没焦距的眼睛,瞳孔松散,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。他确实是个瞎子。
可他脸上没有一丝波涛,安静得像一口千年古井,好像眼前这黑漆漆的一群人,不过是几缕穿堂而过的风。
张二郎刻不容缓地冲上前,评头论足地将工作添枝加叶、颠倒是非地说了一遍。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兄长名节不平的烈士,把柳三娘和徐进说成是早就勾搭成奸的狗男女。
终究,他一把将死后的柳三娘拽到前面,指着她说:“陈瞎子!你不是声称看相最准吗?今日就请你当着大伙儿的面,给咱们瞧瞧!瞧瞧我这个好嫂子,她究竟是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妇人!她那眼角的纹理里,究竟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!”
陈瞎子没有马上答复。他缄默沉静着,那双灰白的眼睛“望”着柳三娘的方向。整个屋子里万籁俱寂,只听得到世人严重的呼吸声和自己的心跳声。
过了良久,他才朝着柳三娘的方向,悄悄招了招手,那沙哑的声响再次响起:“这位娘子,你走近些。”
柳三娘的身体现已生硬得不像自己的了。她被人从后边推了一把,踉跄着往前挪了几步,停在离陈瞎子三步远的当地。她感到一切人的目光都像针相同扎在她背上,又烫又疼。她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陈瞎子并没有像世人幻想的那样,马上就去“看”她的眼角。他安坐不动,那张没表情的脸转向她,慢吞吞地问了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。
这一句平铺直叙的问话,像一把钥匙,猝不及不及地翻开了柳三娘心中那道紧闭的闸口。这两年一切的辛苦,一切的委屈,一切的强撑,瞬间涌上心头。她的鼻子猛地一酸,眼泪差点就掉下来。她死死地咬住嘴唇,用力地址了允许。
柳三娘浑身一震,猛地抬起头,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盲眼白叟。这是她最大的隐秘。这两年来,她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,夜里总是被各种噩梦和纷杂的忧思吵醒,独自一人睁着眼直到天亮。这件事,她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。他是怎样知道的?
陈瞎子的终究一个问题,像一记重锤,狠狠地砸在了柳三娘最柔软的心防上。她再也不由得了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不受操控地涌出眼眶。但她没有哭作声,仅仅死死地咬着唇,听凭泪水无声地滑落。
陈瞎子站启航,渐渐走到她面前。他伸出那只干燥得像鹰爪相同的手,并没有碰到她的皮肤,而是在离她眼角约莫一寸远的当地,停住了。他的手指,在空气中虚虚地“接触”着,好像在感受着那里无形的气场和纹理的走向。
柳三娘从开端的极度惊骇和耻辱,到被他一连串直击心里的问题问得心神含糊,此时,她站在那里,听凭泪水流动,心中竟升起一丝奇特的感觉。她好像不再是被人审判的罪人,而是一个被完全看穿了一切辛苦和假装的不幸人。
全场的人,包含张二郎在内,全都屏住了呼吸,死死地盯着陈瞎子的一举一动,等候他开口,说出那个决议柳三娘命运的终究判词。
时刻好像被拉成了细长的丝线,每一息都充满了折磨。柳三娘的心跳得好像擂鼓,她能明晰地听到自己血液奔腾的声响。
总算,陈瞎子那干燥的手指,渐渐地收了回去。他退后一步,从头坐回那张太师椅上,宣布一声细微的“吱呀”声。
他清了清嗓子,慢吞吞地开了口。声响不大,却像一颗石子投入静水,明晰地传到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
“老朽观你气色,看你纹理……你这眼角的纹,俗称‘鱼尾纹’,人上了年岁,或是劳累过度,人人都会有。仅仅你的鱼尾纹,纹理细密,且多向下走,这是终年忧思悲伤,肝气郁结所造成的。此纹,谓之‘愁闷纹’。”
听到这儿,一些心肠稍软的街坊邻里,渐渐的开端面露不忍。是啊,柳三娘这两年过的是什么日子,咱们众所周知。一个女性家,死了老公,拉扯着幼子,守着个铺子,眼角能没有愁闷纹吗?
张二郎的脸上则闪过一丝不耐烦。他要听的不是这个!他要听的是“”、“不贞”之类的判词!
“仅仅,你这‘愁闷纹’的深处,纹理的走向,却又有些散乱,并不完全顺利。且在那纹理止境,隐约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暗色,此乃……”
“什么?桃花煞?”“天啊!还真是让他说中了!”“桃花煞……那不便是……便是动了春心,犯了淫邪的意思吗?”
张二郎像是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蜜糖,整个人都振奋得颤抖起来。他猛地一拍大腿,像是得了圣旨一般,狂喜地尖叫起来:
“‘桃花煞’!大伙儿都听见了吧!都听见了吧!陈瞎子亲口说的,是‘桃花煞’!我就说我没委屈她!她便是个水性杨花、不守妇道的女性!这便是依据!铁证如山!”
他指着柳三娘,像一头捕到猎物的饿狼,对周围的人嘶吼着:“我没说错吧!她心里早就有了野男人了!还在这装不幸!装无辜!”
之前那些还对柳三娘抱有一丝怜惜的人,此时也完全动搖了。置疑、鄙夷、轻视、乐祸幸灾的目光,像很多把淬了毒的刀子,齐刷刷地射向柳三娘。
“啧啧,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“亏我还觉得她不幸,本来都是装的。”“寡妇门前对错多,古人说的话,真是一点不假啊!这下没话说了吧,连神仙相同的陈瞎z都看出来了!”
柳三娘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,耳边嗡嗡作响,一切人的声响都变成了含糊的噪音。她不理解,为什么?为何会是这样?自己分明什么都没做,为什么连一个素不相識的瞎子,也要这样宣判她的死刑?
她浑身的力气好像在这一会儿被完全抽空了。完了,一切都完了。名声、洁白、茶馆……一切她拼了命想要看护的东西,都在“桃花煞”这三个字面前,碎成了齑粉。
她失望地闭上了眼睛,那串一向强忍着的、滚烫的泪珠,总算决堤而下,带着她终究的一丝期望和庄严,摔得破坏。
张二郎见状,愈加满意忘形。他站到人群中心,振臂高呼,好像自己是正义的化身:“这样的女性,不配留在咱们清河镇!咱们清河镇民风淳朴,容不下这种损坏家声的!把她赶出去!把她的铺子收回来!绝不能让她玷污了我大哥的名声!”
人群的心情被完全鼓动起来,开端骚乱,有几个无赖乃至开端朝柳三娘的方向推搡,眼看着就要失控。
一向不动,好像置身事外的陈瞎子,忽然举启航边靠着的一根陈腐的竹杖,竭尽力气,在堂屋坚实的青砖地面上,重重一顿!
陈瞎子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,第一次,显露了一丝近乎嘲讽的冷笑。他渐渐地抬起头,那双毫无气愤的灰白眼球,径自“望”向了张二郎地点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