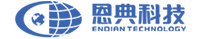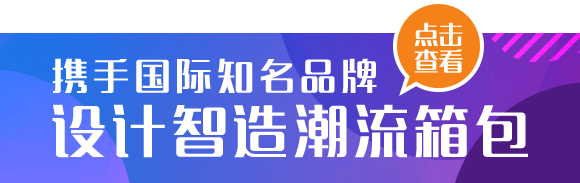声明:本文根据前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造,部分情节、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,旨在出现前史故事的戏曲张力,不代表前史肯定实在。请读者理性看待,勿将虚构情节与前史事实混杂。
1996年的寒冬,河北行唐县庄头村,寒风凛冽,卷着枯黄的落叶在地上打转。这一天,村里的老寿星付香玉走了,享年85岁。
原本,喜丧在乡村是件考究局面的事,吹吹打打,热热闹闹送白叟最终一程。可付家这场凶事,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和苍凉,成了十里八乡茶余酒后谈论的焦点。
原因无他,只由于白叟在临终前,神志清醒地立下了一个让人没办法了解的规则:她不穿寿衣,要穿63年前出嫁时的那套红嫁衣下葬。

灵堂里,那抹鲜红在一片缟素中显得分外扎眼。干燥的尸身裹在褪色的红绸里,脸上涂着厚厚的胭脂,乍一看,不像是个死去的白叟,倒像个等着上花轿的新娘。来吊唁的乡民们目光躲闪,凑在一起交头接耳。
“造孽啊,守了一辈子活寡,死了还要穿成这样,也不怕到了底下那个男的不认她。”
跪在灵前的长孙崔建强,听着这些尖锐的闲话,拳头死死地攥着。他的手心里,握着奶奶咽气前硬塞给他的一个小布包。
那布包里硬邦邦的,没人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,就像没人知道,奶奶这六十三年究竟是靠什么信仰撑下来的。奶奶临走时那个目光,直勾勾地盯着门口,像是在等谁开门进来,又像是透过虚空,在看一段被年月掩埋的本相。
崔建强心里憋着一股火,也藏着一个巨大的疑问:爷爷崔志尧,究竟去了哪里?为什么奶奶至死都深信他还活着?
那年初,世风乱,人心也乱。付香玉那年才17岁,正是如花似玉的年岁,却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要嫁给邻村崔家那个“二少爷”。
出嫁前一天晚上,付香玉躲在被窝里哭肿了眼。她尽管没读过书,但也听村里人说过,那崔家是书香门第,规则大得很。崔家老太爷那是前清的一号人物,家里曾经有田有地,大门大户的。
付香玉惧怕,怕自己这个庄稼院里长大的丫头,到了那种大户人家受欺压,更怕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公是个死板严峻的老学究。
母亲在旁边一边给她梳头一边劝:“香玉啊,那是好人家,尽管这两年传闻衰落了点,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那崔家二郎是个读书人,读书人知书达理,不会打老婆的。”
付香玉抹着眼泪,心里忐忑不定的。那时分的她哪里知道,这桩婚事,成了她这一辈子悲欢离合的起点。
花轿落地,锣鼓喧天。付香玉头上顶着红盖头,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安全果,手心里满是汗。她被人牵着跨火盆、拜天地,整个人晕晕乎乎的,像个提线木偶。
比及入了洞房,周围安静下来,她坐在床沿上,心都要跳到喉咙眼了。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有人走了进来。脚步声很轻,不像是个粗鲁汉子。
一杆秤挑开了她眼前的红布,朦胧的油灯亮光一会儿刺进眼睛里。付香玉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,抬眼一看,愣住了。
站在她面前的男人,穿戴一身长衫,尽管布料旧了些,却洗得干干净净。他长得文雅白皙,眉眼里透着一股温润的书卷气,正笑吟吟地看着她。这便是她的老公,崔志尧。
“饿了一天了吧?”崔志尧的声响温温和和的,回身从桌上拿了一块糕点递给她,“先吃点垫垫。”
崔志尧叹了口气,在她身边坐下,轻声说:“你别怕。我知道外面传咱们家规则大,其实那都是老皇历了。现在家里……说实话,挺难的,你要是嫁过来觉得冤枉,也是应当的。”

付香玉听他这么一说,心里反倒结壮了些。她小声说:“我不冤枉,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。”
崔志尧看着她,眼里闪过一丝亮光,遽然伸手悄然摸了摸她身上的红嫁衣,感叹道:“这赤色衬你,真美观。今后若是有时机,咱们日子过好了,我定让你常穿新衣裳。”
婚后的日子,并不像付香玉想的那样金衣玉食。相反,崔家确实是个烂摊子。公公身体欠好,终年吃药,家里大大小小的工作都要钱。
崔志尧尽管是个大户人家的读书人,却并没有那些少爷的架子。他白日在外面奔走,教学贴补家用,晚上回来还要照料患病的父亲。
付香玉是个勤快人,她把家里家外料理得有条不紊,从不叫苦。她知道老公在外面不容易,自己能做的,便是让他回家能喝上一口热乎水,吃上一口热乎饭。
付香玉蠢笨地学着,笑着问:“当家的,我学这劳什子干啥?我又不去考状元。”
崔志尧正色道:“香玉,人活一世,不能当睁眼瞎,外面的世风在变,咱们得懂道理。你学会了字,今后就算我不在家,你也能看得懂信件。”
崔志尧笑了笑,没接话,仅仅目光里多了一层付香玉看不明白的深意。那时分,他还教她唱歌谣。不是那些情情爱爱的小调,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词儿。
付香玉一边纳鞋底一边跟着哼,她不明白什么叫斗地主,只觉得老公唱这歌的时分,眼睛里像是有火在烧,亮得吓人。
“香玉,你记取。”有一天晚上,崔志尧遽然捉住她的手,很认真地说,“咱们这日子尽管苦,但只需大家伙儿都站起来,总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的。我做的工作,或许现在你看不到优点,但那是为了今后,为了咱们的孩子,为了千千万万像咱们相同的贫民。”
付香玉似懂非懂地允许:“只需你觉得对,我就依你。横竖你是有大学识的人,比我看得远。”
那两三年,是付香玉这辈子最快乐的韶光。尽管穷,尽管累,但身边有知冷知热的人。她觉得,这便是一辈子了。只需守着这样的一个男人,吃糠咽菜也是甜的。
可好景不长,那个动乱的时代,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,也容不下一个小家的安定。
先是家里几亩薄田由于还账卖了个精光,接着是拉车的那头老骡子掉进河里淹死了。这难如登天原本就绰绰有余的崔家来说,简直是塌天的大祸。
那天晚上,崔家的大哥在屋里上吊了。人救下来的时分身子都硬了。一家人哭得呼天抢地,付香玉抱着吓坏了的小姑子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崔志尧跪在大哥的尸身前,磕了三个响头,额头上满是血。他没哭,但付香玉看着他的背影,觉得他比哭还要难过。那是他亲大哥啊,是被这吃人的世风活活逼死的。
办完大哥的凶事,崔志尧变得更忙了。他常常十天半个月不着家,偶然回来一次,也是仓促忙忙,身上还带着泥土和草屑,有时分衣服上更难以想象的是血迹。
付香玉尽管是个妇道人家,但她不傻。她模糊猜到老公在干什么大事,那些深夜悄然来家里找老公的人,一个个目光警觉,说话都压着喉咙。
“我不去谁去?那些学生还在等我,那儿的联络点不能断!”崔志尧的声响尽管不大,但直截了当。
见付香玉进来,两人马上住了嘴。崔志尧接过茶碗,手有些悄悄颤栗。等那人走了,付香玉关上门,拉住老公的袖子,声响发颤:“志尧,你跟俺说实话,你该不会是在外面……干那个?”
她指了指外面,没敢说出“革新”两个字,但在那个时代,这两个字意味着掉脑袋。
崔志尧缄默沉静了好久,反手抓住妻子的手,掌心滚烫:“香玉,我对不住你,原本该让你过安生日子的。但是你看,大哥死了,爹病成这样,咱们村里多少人连饭都吃不上。这世风假如不改,咱们永久没生路。”
崔志尧把她搂进怀里,悄然拍着她的后背:“定心,我心里有数。我还要看着咱们的孩子出世呢。”
那时分,付香玉现已怀了身孕。肚子一天天大起来,这成了全家仅有的盼望和喜气。崔志尧每次回来,都要趴在她肚子上听半响,脸上显露可贵的笑脸。
“要是男孩,就教他读书救国;要是女孩,就让她像你相同贤惠。”崔志尧笑着说。
1933年的一个深夜,外面下着大雨,雷声轰隆隆地响。一阵短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付香玉。
崔志尧翻身而起,动作利索得不像个读书人。他并没有马上去开门,而是先凑到窗户边往外看了看,然后敏捷穿好衣服,回过头抵挡香玉说:“香玉,别作声,我要走了。”

“这儿待不住了,有人出卖了音讯,我要搬运。”崔志尧语速很快,目光里满是着急和不舍,“你听好,我这一走,不了解什么时分能回来。家里这几本书,还有这些信,都是要命的东西。假如三天后我没回来,你就把它们烧了,千万别让人看见!”
崔志尧咬了咬牙,从怀里掏出几块大洋塞进她手里:“这钱你拿着,藏好,别让人知道。照料好爹,照料好自己。等风头过了,我必定回来接你!咱们一家团圆!”
崔志尧决然掰开她的手指,捧着她的脸,深深地看进她的眼睛里,像是要把她的姿态刻在骨头上:“香玉,信我!我崔志尧这辈子不负全国,也不负你,等我回来!”
闪电划过夜空,照亮了他决绝的背影。付香玉赤着脚追到门口,只看见一片乌黑的雨夜,哪里还有老公的影子?
那天之后,付香玉就像丢了魂。她依照老公的吩咐,把大部分信件都烧了。但是,当她拿起那本老公最爱看的书时,手却怎样也松不开。那是老公素日里给她讲故事用的书,上面还有他的批注,笔迹苍劲有力。
她找来油纸,把那几本书包了一层又一层,然后趁着夜深人静,把墙角的砖抠下来几块,掏了个洞,把书塞进去,再用泥巴细细地糊好。
付香玉看着襁褓里的孩子,又哭又笑:“你爹要是看见了,指不定多快乐呢。闺女啊,你要乖,等你爹回来,让他给你起个好名字。”
她给孩子取名叫“忙妮儿”。意思是妈妈太忙了,又要种田又要服侍白叟,还要等你爹回来。
村里人开端指指点点。有人说崔志尧是“革新党”,被官府抓去枪决了;也有人说他跑到大城市去了,早就忘了家里的糟糠之妻。
这些闲话传到付香玉耳朵里,像针扎相同疼。但她不信,她记住那天晚上的目光,记住那句“等我回来”。
忙妮儿四岁那年,遭了灾。先是发高烧,后来身上起了红疹子,上吐下泻。那时分乡村弹尽粮绝,付香玉背着孩子跑了几十里山路去求医,头都磕破了,大夫仅仅摇摇头:“送来的太晚了,准备后事吧。”
回到家,看着孩子在炕上只要进的气没有出的气,付香玉心如刀绞。孩子模模糊糊地喊着:“娘,我要爹……爹啥时分回来给我买糖吃?”
付香玉把脸贴在孩子滚烫的额头上,泪水打湿了枕头:“快了,快了,你爹就快回来了,等你爹回来,给你买一车糖。”
但是,忙妮儿毕竟没比及那颗糖。孩子走的时分,眼睛还睁着,直勾勾地看着门口,像是在替母亲守望那个归人。
掩埋了女儿,付香玉大病了一场。她在炕上躺了半个月,滴水不进,整个人瘦得脱了相。
娘家人来了,看着这个一贫如洗的破宅院,看着形销骨立的付香玉,疼爱得直掉泪。
“香玉啊,跟娘回家吧。”老母亲哭着劝,“孩子没了,男人也不知死活。你才二十多岁,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娘给你再说个婆家,咱不图大富大贵,就图个知冷知热的人,别在这守活寡了。”
“你傻啊!那个崔志尧要是活着,早就回来了!这都几年了?一点信儿都没有,他便是把你忘了!或许早就死在外面了!”嫂子在旁边恨铁不成钢地骂道。
听到“死”字,付香玉像被踩了尾巴的猫,猛地坐起来,沙哑着喉咙喊:“他没死!他也没忘!他说过让我等他,他就必定会回来!生是崔家的人,死是崔家的鬼,我哪也不去!”
从那今后,付香玉把自己封在这个小宅院里。她过继了小叔子家的孩子崔大平,把他当亲生儿子养。她拼命干活,下地种田,织布换钱,替老公尽孝,给公婆养老送终。

每到除夕夜,付香玉总会多摆一副碗筷。对着空荡荡的座位,絮絮不休地说这一年的收成,说孙子又长高了,说村里谁家又娶了媳妇。
改革开放了,日子好过了。孙子崔建强长大了,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他从小听奶奶想念爷爷的故事,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在他心里,那个爷爷便是个抛妻弃子的负心汉,可看着奶奶那执着的目光,他又不敢说破。
1996年,一场意外的大火烧了付家的老屋。85岁的付香玉为了抢救那个藏在墙里的布包,被严峻烧伤。
付香玉吃力地睁开眼,污浊的目光在人群里搜索了一圈,最终落在孙子脸上。她嘴唇活动着,声响弱小得像蚊子哼:“志……志尧……回来了吗?”
崔大平凑到老太太耳边,大声说:“娘!回来了!爹回来了!咱们也找到爹的信儿了,他在外面当了大官,这就要接您去享乐呢!仅仅路远,还在车上,得过两天才能到!”
谁知付香玉听了这话,目光忽然亮了一下,那光荣回光返照般惊人。她好像信任了,又好像底子没信。她颤巍巍地伸手指了指床头的柜子:“衣裳……穿……红嫁衣……”
“不!”付香玉忽然竭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,那声响凄厉得让人心颤,“穿嫁衣!他……他说过……我穿赤色……美观……他……认得……”
拗不过白叟最终的执念,家人只能翻出压箱底的那套红嫁衣。那是当年她出嫁时穿的,尽管保存得好,但毕竟六十多年了,有些当地都脆了。
给白叟穿戴整齐后,付香玉显得反常慈祥。她不再看门口,而是闭上了眼,嘴角好像带着一丝笑意,似乎回到了十七岁那个夜晚,那个墨客挑开了她的盖头,夸她美观。
跟着最终一口气咽下,付香玉走了。带着六十三年的等候,穿戴那身红嫁衣,去赴一场迟到的约会。
葬礼办完的那天晚上,崔建强一个人在收拾奶奶的遗物。除了那件红嫁衣,最宝贵的便是奶奶最初拼死护住的那个布包。
布包被火燎掉了一角,黑乎乎的。崔建强小心谨慎地翻开,里边是一层又一层的油纸。剥开油纸,掉出来几本泛黄的线装书,还有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。
那纸现已脆得快要碎了,上面模糊是爷爷崔志尧的笔迹。崔建强凑在灯下细心辨认,这好像是一封没有来得及寄出的家书,或许是顺手的笔记。
信纸的反面,有一行用铅笔仓促写下的字,笔迹马虎,显然是在极端紧迫的情况下写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