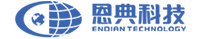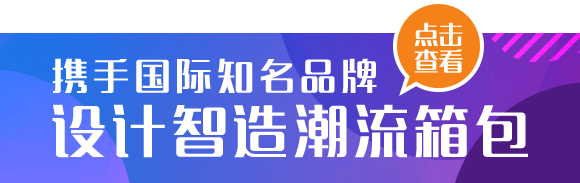江河常常想,他这辈子,便是澜沧江里的一块石头。苏婉秋是天上掉下来的月亮,有一晚,月亮掉进了江里,正好落在他身边。石头动了心,想把月亮留住。
后来,月亮仍是走了。江河才理解,老三说得对。他便是块石头。他留不住月亮,月亮也不属于他。他仅有能做的,便是沉在江底,在每个没有月亮的夜里,想她。
一九七五年的夏天,云南红旗农场的空气是黏的,能粘在人皮肤上。橡胶林里,知了声嘶力竭地叫,如同要把命都叫出来。林子深处,江河蹲在地上,手里捏着一棵草,给上海来的女知青苏婉秋看。
“这个,叫龙胆草,是好东西,清热解毒。你看它的叶子,是两片两片对着长的,不会错。”江河的声响很低,像林子里吹过的风。他皮肤被太阳晒得乌黑,眼睛却亮得像晚上的星星。他是农场里公认最好的猎手,也是干活的一把能手,一个人能顶两个人用。
苏婉秋也学着他的姿态蹲着,白皙的脸上渗着一层细密的汗珠,像清晨的露珠。她来农场快一年了,仍是那么白,像是用上海的雪花膏捏出来的人儿,跟这片红土当地枘圆凿。她的大眼睛仔细地看着那棵草,又看看江河。
江河被她看得有点欠好意思,乌黑的脸膛上泛起一丝赤色。他挠了犯难,说:“我爹教的。咱们这儿山里长大的,都懂这个,不明白就活不下去。”

他们的事,在农场里不算隐秘。谁都知道,江河宠爱这一个上海来的女知青。知青们吃大锅饭,没什么油水,江河就会在半夜里,一个人摸进深山。他打到了野鸡,会悄然炖好了汤,用一个铝饭盒装了,半夜里绕开巡查的人,悄然放在女知青宿舍的窗台下。第二天,苏婉秋就会把饭盒洗得干干净净,放在老当地,里边有时会多两个白面馒头,那是她从自己牙缝里省下来的。
苏婉秋呢,她会就着那盏烟熏火燎的煤油灯,一字一句地给江河读诗。那些诗,江河一句也听不明白,什么“撑着油纸伞”,什么“丁香相同的姑娘”,他觉得不可思议。但他喜爱听苏婉秋的声响,软软的,糯糯的,像他小时分吃过的麦芽糖,一向甜到心里去。他还喜爱看她读书时仔细的姿态,煤油灯的光跳动着,照着她长长的睫毛,在他心里投下一片温顺的影子。
江河不怎样会说话,嘴拙。他花了一个多月,找了一块上好的楠木,那是他在山崖边上发现的。每天晚上等他人都睡了,他就坐在床铺上,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,用一把小小的刻刀,一点一点地刻。木屑落在被子上,他第二天一大早再悄然抖掉。他的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,破了,又长出新的茧子。
他给苏婉秋刻了一只小鸟,小鸟的翅膀完全打开,尾巴翘着,像是下一秒就要挣脱手心,飞向天空。
他把木鸟交给苏婉秋的时分,严重得手心满是汗。他把木鸟塞到她手里,憋了半响,才说出一句话,声响小得像蚊子叫。
苏婉秋的眼睛一会儿就红了。她把那只润滑的木鸟紧紧攥在手心,那只鸟的概括,硌得她手心有点疼。她低下头,从自己那个打了好几块补丁的布包里,拿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深蓝色丝绒盒子。这在其时的农场里,是个稀罕物件。
盒子里,静静地躺着一支簇新的“英豪”牌钢笔,金色的笔尖在暗淡的光线下闪着光。
“江河,这是我爸在我来云南前送给我的。你藏着。”她把钢笔连同盒子,一同塞到江河那双由于终年干活而粗糙无比的大手里,“等你学会写许多字,就给我写信。写一辈子。”
江河看着那支钢笔,觉得它比自己打到的最美丽的孔雀的茸毛还要美观。他觉得,这支笔有千斤重。
他们的好,像橡胶林里的野花,悄然地开,却瞒不过有心人。那个人便是农场革委会马主任的儿子,马伟。马伟从苏婉秋第一天坐着货车,扎着两条麻花辫下来的时分,就惦记上她了。他仗着自己爹的权势,在农场里横着走,没人敢惹。他天天在苏婉秋跟前晃悠,今日送一罐橘子罐头,明日塞两块大白兔奶糖,苏婉秋从来没正眼瞧过他,东西也原封不动地退回去。
马伟在知青们面前丢了体面,心里窝着火。他看着江河和苏婉秋在橡胶林里出双入对,那目光阴得能滴出水来,像一条躲在暗处的毒蛇。
秋天来了,气候凉快了些。农场里的橡胶树开端大片大片地落叶,铺在赤色的土地上,踩上去沙沙地响。一个音讯,像平地里起了一声雷,炸响在整个农场。
整个知青点都疯了。那些素日里萎靡不振的知青们,一个个眼睛都红了,像是饿了好久的狼,看到了肉。谁都想脱离这个又湿又热的鬼当地,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城市,回到爸爸妈妈身边。为了一个目标,人们开端各显神通,套近乎,走后门,乃至相互揭露,把素日里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捅了上去。

苏婉秋的脸上,也露出了又快乐又杂乱的表情。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宿舍门口发愣,看着远处的群山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江河的心,像被一块大石头压住,一会儿就沉到了底。那天晚上,他把苏婉秋叫到他们常常见面的那片橡胶林里。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在地上,斑斑斓驳的。
苏婉秋看着他,眼睛躲躲闪闪的,不敢跟他对视。她低着头,玩弄着自己的衣角。
江河不说话了。他还能说什么呢?他知道,自己给不了苏婉秋上海的日子。他只需这一身力气,和这片他永久也离不开的红土地。他连带她去县城看一场电影,都得策画好几天。而上海,那是另一个国际,一个他只在苏婉秋的描绘里听说过的,用磷寸一点就亮的电灯,和跑得飞快的轿车的国际。
马伟的活动更频频了。他公开在知青点放话,说谁要是能帮他压服苏婉秋,他就让谁也上返城的名单。他还直接找到苏婉秋,拍着胸脯说:“婉秋,只需你点个头,我爸就能把你的目标搞定。第一个便是你。”
那段时刻,苏婉秋开端频频地收到家里的来信。邮递员每次送来信,她都像是捧着什么棘手的东西,马上跑回宿舍。等她再出来的时分,眼睛总是红红的。
她的眉头,一天比一天皱得紧,像是有什么化不开的心思。她和江河在一同的时分,话也变少了,常常说着说着就走了神。有时分,江河看着她,觉得她离自己很远,远得像天上的云,他伸出手,却怎样也抓不住。
江河心里很不安,像是有蚂蚁在爬。他觉得,苏婉秋有事瞒着他。他觉得,有什么欠好的事,就要发生了。
返城名单发布的那天,农场的喇叭里放了一上午的《咱们工人有力气》。知青点的门口,围了一大圈人,把那张贴着名单的大红纸围得风雨不透。
“是啊,放着主任的儿子不要,跟一个本地的泥腿子,图什么呀。人家上海姑娘,精明着呢。”
那些话,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,一刀一刀地扎在江河耳朵里,扎得他血肉含糊。他疯了相同,拨开人群,冲到女知青点。
宿舍里很乱,咱们都在忙着贺喜,或许为自己没选上而哭泣。他一眼就看到了苏婉秋。她正背对着门口,默默地拾掇着自己的东西。她的床铺现已空了,只剩下一床卷起来的,打了好几个补丁的铺盖。
“是真的吗?”江河的声响抖得凶猛,像风中的落叶。他不敢信任,也不愿意信任。
苏婉秋没有回头,她的膀子一耸一耸的,像是在哭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猛地转过身。
“江河,咱们不是一个国际的人。”她看着他,一字一句地说,“我要回我的上海了,那里有楼房大厦,有抽水马桶,有我的未来。我不能一辈子待在这个又穷又破的当地。”
江河觉得,自己像是被一道平地风波劈中了。他看着眼前这个既了解又生疏的女孩,心像被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,来来地割。他的自豪,他的自负,在这一刻,被碾得破坏。
他认为他们的爱情,像这大山里的石头相同巩固。他没想到,在回城的目标面前,这么一触即溃。
“好,我忘了你。”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,眼睛红得要滴出血来,“上海的大小姐!”
那天晚上,送行返城知青的军用货车来了。车上载着知青们的欢声笑语,和他们对未来的神往。苏婉秋坐在车上,没有回头。
江河一个人跑到澜沧江边。月亮很大,很圆,照得江面上一片雪白。江水哗哗地响,像是在哭,又像是在笑。
他从口袋里,掏出了那支“英豪”牌钢笔。它在月光下,闪着严寒的光。他想起她把钢笔交给他时,眼睛里的光。
钢笔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,然后“噗通”一声,掉进了汹涌的江水里,溅起一朵小小的水花,就再也看不见了。

几天后,江河像丢了魂相同。他不吃不喝,整天躺在自己那间黑漆漆的屋子里。他最好的朋友老三看不下去了,端着一碗米线找到了他。
“哥,这是我在送知青那条路旁边的水沟里捡的。信封都烂了,看姿态是苏婉秋走得急,从包里掉出来的。地址是上海寄过来的,收信人是……是苏婉秋。”
看到信上的内容后,江河震动了,手都开端颤栗!那娟秀的笔迹,是他见苏婉秋仿照过的,是她母亲写的。
信纸被水泡过,又被泥水浸染,笔迹有些含糊了。但上面的内容,每一个字,都像一块烧红的烙铁,狠狠地烫在了江河的心上,烫得他浑身颤栗。
“婉秋,我的女儿,家里出大事了。你爸……你爸由于一篇许多年前写的文章,又被揪出来检查了。这次来势汹汹,说要从头定性,随时有或许被定性为‘敌我矛盾’。你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。咱们家现在天都快塌了,我和你弟弟每天都活在惊骇里。”
信里接着说:“就在咱们穷途末路的时分,你们农场的马主任,经过联络联络上了咱们。他说,他有才能在上海疏通联络,找人把你爸的工作‘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’。可是,他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他的条件是,你有必要马上拿到返城目标,回到上海,嫁给他的儿子马伟。婉秋,我的女儿,是妈没用,是妈对不住你。但为了你爸,为咱们这个家,你只能献身自己了。你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咱们这个家就完全完了。”
“那个农场的穷小子,你就忘了吧。你们的未来,妈看不到一丝期望。他维护不了你,只会连累你一辈子。听妈的话,就当是为咱们这个家,献身你一个人吧……”
她的决绝,她的冷漠,她说的那些伤人的话,全都是演给他看的。她知道他的脾气,火爆,激动。假如他知道了本相,他一定会拿着砍刀去找马伟拼命。以马家在农场的实力,他江河,只需死路一条。
江河瘫坐在地上。这个从小到大,在山里跟野猪奋斗,摔断了骨头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汉子,第一次,像个无助的孩子相同,声泪俱下。
心里的痛,比被她当面扔掉的时分,还要痛上一千倍,一万倍。那是一种混杂着懊悔、自责、和撕心裂肺的力不从心的疼痛。
他哭够了,从地上爬起来,用袖子狠狠地擦干了脸上的眼泪和鼻涕。他的目光里,燃起了两团火。一团是复仇的火焰,另一团,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决计。
这十年里,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知青们都像落潮的海水相同,回到了自己的城市。改革开放的春风,吹遍了这片陈旧的土地,也吹绿了江河承揽的那片茶山。
江河没有沉沦。那封被他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,藏在贴身口袋里的信,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仅有动力。他像一头不知道疲倦的黄牛,在自己的土地上张狂地干活。他人一天割十个小时的橡胶,他就割十二个小时。他成了农场最年青的生产队长。

后来,农场搞家庭联-产承揽责任制。他第一个站出来,用自己一切的积储,又跟亲属和朋友借了一圈,承揽了农场后山最大的一片茶园和药材地。
凭着从父辈那里学来的种茶手工,和自己探索出来的草药常识,加上他那股不要命的苦干劲头,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他不再是那个只会静心干活的愣头青,他学会了跟南来北往的商人打交道,学会了讨价还价,学会了看清人心。
到了一九八五年,他现已成了家喻户晓的“万元户”,是当地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。他盖了新房子,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,成了村里第一个有电视的人。
他没有成婚。无数人给他提亲,美丽的姑娘也不少,他都客客气气地拒绝了。老三劝他:“哥,都十年了,苏婉秋早便是他人老婆了,你还等什么?”
江河仅仅摇摇头,不说话。他的心里,只装着一个人。一个他既爱又恨,既疼爱又内疚的人。
这些年,他一边赚钱,一边托各种联络,探问苏婉秋在上海的音讯。他找那些返城的知青,给他们寄钱,寄土特产,只求他们能帮助探问一下。
总算,一个当年联络还不错的返城知青回农场省亲,给他带来了一个切当的地址。
江-河把生意和家里都交给了老三,带上他十年里攒下的一切积储,换了一身他最好的衣服,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。
火车“何况何况”地走了三天三夜。上海,这个他只在苏婉秋口中听说过的繁华都市,让他感到既生疏又敬畏。楼房,轿车,穿戴时尚的人群,都让他目不暇接。
他依照地址,找到了一个典型的石库门胡同。胡同很窄,两头的房子挤在一同,头顶上是鳞次栉比的晾衣杆,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,像万国旗。
“苏家?哦,侬是说曾经住亭子间额苏教授一家啊。”阿婆抬起头,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这个露宿风餐的外地人。
“哎哟,婉秋啊……真是个不幸的姑娘。”阿婆叹了口气,摇了摇头,“回来没多久就嫁人了,听说是嫁给一个当官的儿子。惋惜啊,没过几年好日子,那家就垮台了。她那个男的,便是个废物,吃喝嫖赌,什么都干,还天天打她。早就搬走了,好几年没见到了。”
“不过,”阿婆像是想起了什么,眯着眼睛看着他,持续说道,“她有个儿子,本年大约九岁了吧,长得却是娟秀,不像他那个混账爹。那孩子,姓名也怪,叫……叫**江念秋**。”